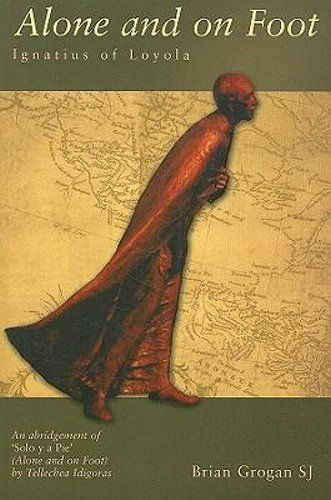耶穌會克里斯托瓦爾.馮內斯 (Fr Cristóbal Fones SJ ) 神父將於2025年接下教宗全球祈禱網絡 (Pope’s Worldwide Prayer Network, PWPN) 國際主任一職。這項宗座工作由教宗方濟各在2018年創立,以在教會的核心以及耶穌聖心的精神中促進祈禱。
教宗任命耶穌會馮內斯神父為教宗全球祈禱網絡新任國際主任
「神操的神學結構」工作坊 港台兩地圓滿舉行
耶穌會士詹姆斯.漢維神父(Fr. James Hanvey, S.J.)近日分別在港台兩地帶領為期五天的「神操的神學結構」工作坊,中華省多位耶穌會士、依納爵靈修輔導、接受過依納爵靈修培訓的校友、使命合作者,以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的學生熱烈參與,在酷熱的夏天裡享受了恩寵滿滿的「神操」饗宴。
教宗方濟各當選10週年紀念:耶穌會弟兄們的反省
2013年的3月13日,來自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教區的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總主教被選為伯多祿的265任繼承人,他以方濟各為名號,是首位來自來拉丁美洲,也是首位選為教宗的耶穌會士。在此10週年之際,我們邀請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士與我們分享教宗方濟各對他們個人、牧靈工作及生活中所帶來的啟發和反思。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LVII
第四十七章:教宗的僕人,1538年 改革無效 一五三七年底,依納爵、法伯爾和雷奈士抵達羅馬,情況沒多大改善。在位的教宗保祿三世是個法爾內賽人,與其說他有天使般的吸引力,不如說有文藝復興的氣質。他在博爾吉亞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扶持下,做過幾個教區的主教,並在一五三四年當選教宗。自此,他對教會改革的關注,不及他對自己家族及兩個兒子的升官晉爵來得熱心。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LVI
第四十六章:「我要在羅馬恩待你」,1537年 被安置與聖子在一起 依納爵死後,翻閱他私人物品的人,在他的筆記中,發現這句重要的話:「當天父把我和祂的聖子安置在一起時」。很明顯,指的拉斯多達,雖然這片語本身不怎樣富啟示性。依納爵不是那種硬要折磨自己去表達那被定義為不能表達的神秘者,卻把烙印默存心中。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LV
第四十五章:主內的朋友,1537年 等待 「現在,他們會分頭前往意大利各地,再用一年時間等待乘船去耶路撒冷的機會。若果天主認為此行去聖地,對祂不是好的侍奉,他們就不再等,繼續致力於他們的服務」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LIV
第四十四章:威尼斯和維琴察,1537年 依納爵晉鐸 從羅馬回到威尼斯後,同伴們重返醫院,繼續慣常的工作。鮑巴第拉、雷奈士、沙勿略、庫杜萊、勞德理格和依納爵於一五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聖若翰洗者慶日,在威尼斯晉鐸。撒爾墨龍因年輕,被祝聖為執事,待下一年六月才能晉鐸。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LIII
第四十三章:從威尼斯到羅馬,1537年 在醫院服務 一五三七年一月八日,同伴們到了威尼斯,見到依納爵,大家都歡喜若狂。他們向他介紹三位新同伴,他亦給他們介紹一些同伴。他們還要等兩個月才能起程去羅馬,請教宗批准他們去聖地。於是,依納爵安排他們在兩所醫院裏服務。要造學問的大學生,投入威尼斯醫院做厭惡性的工作,想必是一種殘忍的生活體驗,需要巨大的內在力量去克服。沙勿略為了克服自己對一名梅毒病人的厭惡,迫自己用舌頭舔他的潰瘍。至於勞德理格,當他得悉醫院拒絕給一名痲瘋病人床位時,便請他睡在自己的床上。後來,沙勿略以為自己因此染了梅毒;勞德理格亦由於擔心自己染了痲瘋病而病了一天。 飢餓的乞丐 經過兩個月在醫院裏的磨練,同伴們起程去羅馬,請教宗祝福他們的耶路撒冷之行。依納爵由於審慎,沒有與他們同去,免得別人起疑心。一方面,他想避開不久前與他相處有些困難的、新近就任樞機的卡拉法;另一方面,他想避開向巴黎宗教裁判所告發他的奧爾提茲博士,後者剛好在羅馬。或許,依納爵特意不跟同伴們一起上路,以作為對他們的考驗。這回,不像從巴黎到威尼斯,同伴們沒有分文,單靠施捨往羅馬去。我們知道,他們到達拉文納時,渾身濕透,筋疲力盡,餓得半死。他們按習慣分成三人一組上路,每組有一位神父,並效法依納爵的榜樣,在收容所或乾草堆,甚至馬棚裏過夜,不帶任何物資,吃施捨得來的。有一次,他們光著腳在滂沱大雨中走了一整天,邊走邊祈禱和唱聖詠;除了清晨吃了一點麵包外,肚子裏再沒有什麼。又有一次,有人誤以為他們是那幫在一五二七年搶劫羅馬的退伍軍人,正要去羅馬求教宗寬恕。 為了購買從拉文納去安科納的船票,他們典當了一本日課,終日捱飢抵餓。在安科納的市場,雷奈士光著腳彬彬有禮地站在一位賣菜的婦人前,感謝她給了他一個蘿蔔、一個捲心菜和一隻蘋果。他們在洛雷托住了三天,潛心祈禱、做靈修。在托楞蒂諾,一個外國人給了他們一份有麵包、無花果和酒的晚餐,他們就與其他乞丐一起享用。他們終於在一五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聖枝主日到了羅馬,分別住進由自己國家所辦的收容所。這四個月,令他們的初學期很不艱苦。 雷奈士後來說, 在這期間,他們度的是依納爵的「生活方式」, 即放棄世俗事物,唯獨依靠天主。 那幾個月是他們生命中最英勇的時期。 教宗歡迎 在羅馬,情況出人意表:原本在巴黎告發依納爵,那可怕的奧爾提茲博士,成了依納爵最強的擁護人,他甚至幫助團體獲得與教宗保祿三世會面的機會。這是一次多麼令人難忘的接見啊!奧爾提茲告訴教宗,他們九人是巴黎最出色的神學家,想以徹底貧窮的方式去耶路撒冷朝聖。他們的故事,非比尋常,幾近神蹟。 教宗保祿三世喜歡接待承諾能增添他餐桌氣氛、首次到訪羅馬的人,與他一起進餐。於是,便邀請了他們。席間,教宗靜聽他們與應邀的其他神學家,進行哲學和神學討論。前幾天還睡在馬棚,來自巴黎的學者,現與教宗同席,與樞機和博士們同坐。教宗保祿三世很喜歡他們,便按慣例,問他們渴求什麼。他們說,他們既不想要錢,也不想要教會職位,只希望能得到他批准他們去耶路撒冷。法伯爾和其他十二位同伴,得到了教宗的批文,准他們去聖地,並留在那裏,但如果他們喜歡離開,隨時都可以離開。此特權可以抵銷方濟會聖地守護長要他們離開耶路撒冷的任何壓力;他曾命令依納爵在一五二三年離開耶路撒冷。他們在一五三四年,在致命山上所發的盟誓,如今要兌現了。 敞開的門 教宗和樞機們給他們籌募了二百六十枚金幣,資助他們坐船去聖地。另外,教宗賦予他們的神父那通常是留給主教的權柄,即赦免某些重罪的權柄。同時,允許他們尚未晉鐸的人,可以從任何一位主教手中,接受聖秩聖事,被祝聖為司鐸,不需要受聖教會的法典所限,省卻拖延的時間。 就這樣,這些奇怪的朝聖者,返回威尼斯,一路繼續行乞;不過,在他們的肩上,那標明他們是乞丐的肩包裏所盛載的特權,卻完全超乎他們的想望。在這些特權當中,最令他們驚喜的,是晉鐸的大門向他們敞開。他們不必附屬於某個教區,可「以自願貧窮並擁有足夠學歷為由」晉升神父。 同年,即一五三七年七月,當依納爵論及這些特權時,寫說: 「同伴們過著極度貧窮的生活,沒有錢,沒有介紹信…… 但是他們一心信靠天主…… 在毫不費力之下,獲得比他們尋求的多……」。 畢竟,他們只求允許去聖地朝聖!這是「主內九位朋友」的經歷,這是依納爵對來自巴黎的同伴們的稱呼。新加入團體的兩名同伴,因不夠堅韌,缺乏定力,而離開了團體,其中一人後來給他們帶來麻煩。 反省: 「他們一心信靠天主……在毫不費力之下,獲得比他們尋求的多……」 請回顧一下,你全心信靠天主,而獲得遠比尋求的多的經驗。 (待續)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LII
第四十二章:從巴黎到威尼斯,1536-37年 異端者? 依納爵的同伴突然中斷學業和使徒工作,並離開巴黎,使許多人不解。大學一位博士以此為良心個案來見法伯爾,不算牽強。博士認為,團體毫無疑問是在巴黎行善,但現在他們放棄所做的好事,冒險追求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出來的計劃。他們就這樣離開巴黎,算不算犯大罪?博士甚至請法伯爾允許他把這案件提交神學院的博士們審理。然而,同伴們去意已決,亦不需要尋求那位依納爵給他們推薦,在急需時可找他保護的要人。畢竟,他們突然離開巴黎,的確酷似逃走的樣子。幾年後,當他們身在意大利,便被指匆匆離開巴黎,與異端者無異。 徒步寒冬 勞德理格記載他們去威尼斯的旅程及途中遇到的危險。為了避開戰區,他們決定走更長更艱難的路,即是要途經德國和翻越阿爾卑斯山。幾個同伴提前五六天出發,留下的要把團體的財產分給窮人。為了避開人們的注意,這最後的小隊,大概是在十一月十五日黎明前離開巴黎。行了一天,他們在晚上遇到一些農民和士兵。他們問他們是誰,從哪裏來,要去哪裏。法籍的同伴們代團體作答,說他們是從巴黎來的學生。但是,他們是隱修士或神父嗎?問到這個問題時,一位矮小的老太太打斷士兵的盤問,說:「哦,讓他們走吧,他們要去改革一些省份呢!」逗得大家開懷大笑,也讓他們繼續上路去了。 從那時起,他們決定,在法國境內,只讓法籍同伴回答別人的提問,而西班牙的同伴只說他們是從巴黎來的學生。這個不變而含糊的答話,使一個盤問他們的士兵,嚷著叫其中一名西班牙同伴為「啞牛」。當然,他們身穿學士長袍,此外,頭戴寬邊帽,手拿朝聖者手杖。每人肩上都挎著皮包,裏面裝著聖經、日課和紙張,胸前還掛著一串念珠。為了方便行走,他們把長袍捲起,掖在腰間的皮帶裏。 勞德理格在四十年後追憶, 仍清楚記得每個同伴對天主的無盡依賴和信心,以及那份異常的快樂。 他們歡欣踴躍,飄飄然,彷彿雙腳從未碰到地面。 兩組人在離巴黎東面二十八英里的一個小鎮會合,在這裏他們決定不再分開,一起走畢全程。與其一路行乞,他們選擇先用光帶在身上的錢,直到抵達威尼斯。一路上他們祈禱,默想,唱讚美詩,念日課。如果有人問他們去哪裏,他們就說去洛林朝聖。在法國,天雨連綿;到了德國,飄雪紛飛。雷奈士說:「我們是遠足的初學生」。此時,他們大概都會對擅於萬里長征,精力旺盛的依納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一路上 他們在途中遇到不少趣事。有一次,勞德理格走散了,結果要跟一名農民打起來,因為那農民要帶他去「見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到了德國,西班牙的同伴代整個團體講話,說他們是來自巴黎的學生,要去洛雷托朝聖:意味著他們要忍受新教徒的嘲弄。如果雪虐風饕是撕裂他們身體的鉗,面對面與新教徒接觸,就是在折磨他們的靈魂。最終他們筋疲力盡到了巴塞爾,需要休息三天,以恢復體力,並為天主教的信仰規條辯護。之後,他們起程往離巴塞爾有一百英里遠的康士坦茨。他們既不懂德文,又不懂當地話,又不熟路,所以多次迷路。 在其中一次,他們誤闖一條信奉新教的村莊。當時是晚上,人們在慶祝當地堂區司鐸的婚禮,在吃喝、唱歌和跳舞。在另一個鎮上,一個已婚司鐸因為同他們辯論輸了,便威脅要把他們投入監獄。在那個可怕的晚上,他們以為自己死定了,可是,有個同情他們的年輕小夥子,幫助他們在黎明前逃脫。在康士坦茨這個完全信奉新教的市鎮,他們幾經辛苦,才得以在一間小聖堂裏,在繳付稅項之後,與信眾一起參與彌撒。 在進入林道之前,有位老太太從一所痲瘋病醫院出來,走到他們跟前,激動地喊叫,企圖親吻掛在他們胸前的念珠。之後,她把她收藏起來的、那些由異端分子砍掉的許多聖人塑像的頭和手,遞給他們看。之後,她陪他們去城門口,向路人喊說:「看呀,你們這些騙子!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們這些撒謊的騙子,不是在告訴我,人人都信奉了新教的謬論嗎?你們撒謊。現在,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我不會再被你們愚弄了!」這位老太太全不為威迫或利誘所動,絕不離棄她一直信奉、源遠流長的宗教。 反省: 勞德理格仍清楚記得每個同伴對天主的無盡依賴和信心,以及那份異常的快樂。 請回顧一下,在一些困難時刻,你竟體驗到對天主完全的信賴 ,並經驗到由此而來的快樂。 (待續)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XXXI
第四十一章:與未來的教宗意見不一,1536年 革新司鐸? 卡拉法主教在一五五四年當選教宗,取名保祿四世。發生在一五三六年的事表明,即使他與依納爵有相同的目標,即成立一個「革新司鐸」團體以幫助教會,但兩人性格不合。他們待人的方式,南轅北轍。卡拉法主教對郝塞斯所做的是陰險的,甚至客觀地說是詆毀。他使跟依納爵做退省的人,心裏極度懷疑依納爵的正統性,甚至企圖要日漸加深他們的懷疑。依納爵和卡拉法主教曾面對面談論,而談話都集中在革新司鐸 ── 這些司鐸名為泰阿蒂尼 ── 屬卡拉法管轄。兩人深入討論這話題時,卡拉法不禁大發雷霆。二十年後,身為教宗的他,仍未能掩飾怒火。 我們從依納爵寄給卡拉法的一封信中,得悉依納爵的觀點。他似乎不關心信的內容是否經過慎思熟慮了,他直率得驚人,以一個平信徒的身分,站在主教面前,請他用情,用善意,用真誠,來接納他的信,如同他懷著同樣的心情寫那封信一樣。 他一開始就指出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卡拉法在一五二四年創立的泰阿蒂尼團體,發展緩慢。「像小人物經常在偉人前做的」,他膽敢道明他認為這團體為何沒有發展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卡拉法自己的生活方式。依納爵說,他可以理解卡拉法作為團體的領袖,因尊嚴和高齡而穿著較好,但他亦相信,「有智慧的做法」,是效法古聖先賢,如聖方濟各‧亞西西和聖道明,給追隨他們的人豎立榜樣。 領導人不應該放縱自己,奢華享樂,而應該以德服眾。 依納爵在《自傳》中, 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申述這個原則。 然後,依納爵談到卡拉法創立的這個新團體本身。他說,泰阿蒂尼太專注於自己的團體,沉醉於詠唱日課,靠人施捨,不出外傳教,不做補贖善功,不肯受乞討的羞辱。依納爵不敢在信中寫下其他更重要的事了。從對泰阿蒂尼這些負面描述來看,我們可以推斷依納爵在他生命的這個階段,對一個理想修會所懷的期望。 千錘百鍊 依納爵對卡拉法坦誠而不留情面的評語,造成了兩個領導人關係破裂的導火線。當卡拉法晉升樞機,並到了羅馬,依納爵將要忍受他赤裸裸的憎惡。依納爵從未透露過他與卡拉法面談的細節,我們只知道,其間他除了批評卡拉法的思想,亦表白了他個人最深的信念。 在他看來, 只有英雄氣慨和行為,才能真正抓住人心,衍生生命。 依納爵夢想造就的是經得起實戰考驗的英雄, 而不是藏身於城市中心的隱修士。 幸好,他留在巴黎的團體,將在一年後重聚,他的夢想不久就要變為現實了。 依納爵留在巴黎的幾位精英,沒有令他失望。雖然他返西班牙休養,令他們難過,但他們的關係非常牢固,好像即使沒有依納爵,團體都會繼續發展似的。他們都專心求學,且持續每週辦告解、領聖體和每天做默想。他們之間的親密情誼,把他們繫在一起,大力支持著每一個人。畢竟,真正使他們團結的是基督,而不是依納爵。這解釋了為什麼依納爵不在,他們仍然在一五三五及三六年,重宣他們在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在致命山上一起宣發的聖願。 新同伴 他們因有三位新同伴加入而欣慰,三人都來自法國,其中傑伊和布諾特已經是神父了。他們透過當時團體中唯一的神父法伯爾,認識這些最早期的同伴。他們以法伯爾為首,他不是長上,也不是第二個依納爵,而是在團體中輩份最高。團體的凝聚力來自大家將神操實踐。法伯爾擅長用依納爵神操的方法待人,他有擅聽告解的殊恩,有真正能同情別人的神恩,所以他吸引了很多人。眾多來向他懺悔的人當中,有一位叫鞏路易‧剛卡威‧卡馬拉,年僅十七歲,是葡萄牙人。依納爵在一五五三至五五年間就是向卡馬拉口授他的《自傳》。 一五三六年十月三日,依納爵在威尼斯時,法伯爾、勞德理格、撒爾墨龍、鮑巴第拉、傑伊、庫杜萊和布諾特都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這個學位雷奈士和沙勿略早已拿到了,但兩人卻未能取得神學碩士學位,因為這要用多幾年時間,而他們打算離開巴黎的日子,即一五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很快就到了。實際上,他們要將這個日子提前到一五三六年十一月,因為法國和西班牙開戰了。離開巴黎前,雷奈士和沙勿略取得曾經在巴黎神學院,讀過一年半神學的一紙證明。 反省: 在依納爵看來,只有英雄氣慨和行為,才能真正抓住人心,衍生生命。 你是否發現自己,總被別人的英雄行爲所折服? (待續)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XXX
第四十章:在威尼斯帶神操和自修,1536年 平靜的一年 在依納爵的生命中,一五三六年是相對平靜的一年。他的健康似乎有了好轉。他在威尼斯有時間讀神學,不過只是自修,因為這個不平凡的城市,竟然連一所大學也沒有。他不必為生計操心勞碌,有「一位非常善良博學的人」供他食宿,此人可能就是西班牙領事。依納爵在一五四零年寫的一封信中,形容他是「一位老朋友兼主內的兄弟」。依納爵在這一年,經常從巴塞羅納的伊莎貝爾‧羅斯爾,及巴黎的朋友,收到救濟品,這使他不用成為任何人的負擔,也不用為食物求乞。他這樣無憂無慮地在威尼斯住了一年。 巴塞羅納的一位老朋友邀請依納爵到巴塞羅納作一系列有關四旬期的講道,依納爵答覆說,儘管他渴望滿足這個城市的需要,因為他欠巴塞羅納的「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但他寧願「以卑微的身分,像個窮人那樣,講授容易理解、不太重要的課題」,並補充說,他一完成學業就會把自己的書寄給伊莎貝爾‧羅斯爾。他在寫給巴黎一位恩人的信中說:「我的身體非常健康,並等待四旬期到來,讓我可以把學業放在一邊,專心於更重要、更持久和更有價值的事」。 信件 在威尼斯,依納爵並沒有把時間全部用來安靜地讀書,獨居的他開始給人寫信,有些信件特別談到教義,例如給巴塞羅納的本篤會修女德肋撒‧納匝德爾寫的兩封信,仔細提到祈禱和分辨神類的指引。若我們細心閱讀,不難在字裏行間,體悟依納爵的個人經驗。在這些威尼斯信件中,他經常談到正在影響別人的考驗,比當事人還要敏銳。他沒有公開批判時弊,並認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會折磨教會,指出她的罪惡。然而,他對教會 ──「耶穌基督真正的淨配」的愛,沒有使他看不見教會的弊端。 一五三六年,依納爵從威尼斯給老朋友即聽告解神父米奧拉博士寫了一封信。米奧拉曾在阿爾卡拉和巴黎幫助過他,但仍對依納爵的未來存疑,並拖延不做神操。 依納爵請求他立刻就做, 「請你做我在以前已請求你的事,因為據我所知神操是人此生既能使自己得益, 又能幫助許多其他人,使他們獲益的最好方法。 即使你覺得自己沒有這個特別需要,但你會看到, 神操將會怎樣出乎你的夢想,幫助你去好好地服務他人」。 米奧拉最終答應了依納爵的請求,做了神操,結果他於一五四五年加入耶穌會。 神操 依納爵亦忙於組織一些讓人可作靈修談話的聚會。這些聚會不僅是熱心教友的聚會,他更願藉此帶人做神操。彷如《若望一書》開首說的,他不能再對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並親手觸摸過的生命的聖言,保持緘默。 他不是在推銷一個學習自制或怎樣保持情緒鎮定的課程, 他想深入人命運的根源, 並已經幫助了很多人看清,什麼是他們最終的歸宿。 他想讓人能夠以感恩和服務的態度走向天主和世界, 這就是神操建築其上的「原則與基礎」。 依納爵給我們留下做了神操的知名人士的大名。後來他給其中一人寫信說:「如果你擁有財產(這位收信人來自非常富裕的家庭),財產不應該擁有你,也不應該讓任何現世事物去擁有你」。此話成了依納爵的座右銘,更多是由於他的個人經驗,而非理論原則,因為正如他坦言的,他一天比一天更能深刻體嘗聖保祿寫的: 我們在任何事上,「像是一無所有的,卻無所不有」 – 格後6:10。 一位來自馬拉加,品學兼備的神職人員,名叫郝塞斯。他一直都想做神操,奈何始終沒有實行。最後,他下定決心;在退省的第三天,坦誠自白,使依納爵十分驚訝:他未做神操前很擔心,怕神操會把一些錯誤的道理教給他,所以他帶備一些書籍,以正視聽。他的態度是因為「有人給他講過某些話」。 可以肯定,這懷疑是卡拉法主教灌輸給郝塞斯的。卡拉法會在不久的將來被任命為樞機,幾年後,又當選為教宗保祿四世。神操使郝塞斯獲益良多,媲美依納爵昔日在巴黎的同伴,並表示願意:「追隨朝聖者的生活方式」。 反省: 「我認爲:神操是人此生既能使自己得益,又能幫助許多其他人,使他們獲益的最好方法。 請反省一下,多年來你爲自己的靈性生命所下的功夫。 (待續)
Alone and on Foot 踽踽獨行 依納爵‧羅耀拉 XXXIV
第三十九章:從羅耀拉去威尼斯,1535年 西班牙之旅 這是依納爵最後一次離開羅耀拉,展開徒步四個月,踽踽獨行的旅程。他首先去方濟各‧沙勿略的家鄉,把沙勿略在巴黎寫的信交給他哥哥,此信為化解他哥哥對依納爵的反感,因為「有些卑鄙的人給他打報告」。沙勿略在信中,讚依納爵不僅「在許多時候,在金錢和人際關係方面幫助我」,而且「他是我放棄狐朋狗友的原因,我因經驗不足,而誤交損友」,並說依納爵是個「了不起的天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