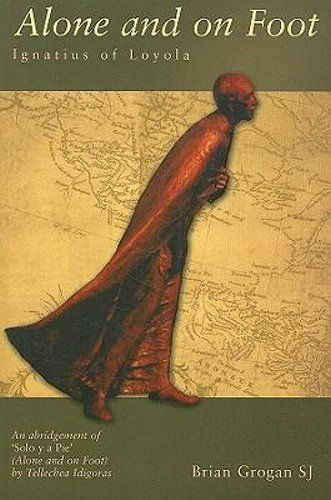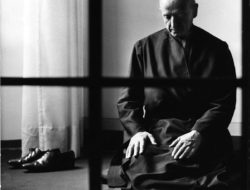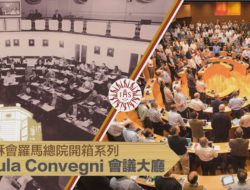第四十七章:教宗的僕人,1538年
改革無效
一五三七年底,依納爵、法伯爾和雷奈士抵達羅馬,情況沒多大改善。在位的教宗保祿三世是個法爾內賽人,與其說他有天使般的吸引力,不如說有文藝復興的氣質。他在博爾吉亞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扶持下,做過幾個教區的主教,並在一五三四年當選教宗。自此,他對教會改革的關注,不及他對自己家族及兩個兒子的升官晉爵來得熱心。
然而,他在樞機團實行的改革,給人帶來希望:他頒授紅帽給傑出的樞機,當中有兩人後來成了教宗,並大力支持耶穌會。一五三六年,許多這些傑出的樞機共同草擬了著名的《教會改革計劃》,指出教會需要矯正的弊端。當中關注教宗權力過大,並起草基本的改革指引,包括:教廷元老的責任、豁免權的限制、未來司鐸的培訓和傳道方式的改良。他們的計劃很嚴謹,表達的很明智,是健全思想與善意的象徵,但也逃不出一紙空文的命運。
教宗保祿三世的確曾命令住在羅馬的主教回到自己的教區,但沒有人執行他的命令。他嘗試召開大公會議,失敗更見明顯。天主教這邊沒有人回應他的要求,在這藐視之上,是新教徒很不客氣地公然拒絕參加任何會議。結果,脫利騰大公會議直到一五四二年才得以召開,第一輪會議更因方濟一世和查理五世的持久戰,而要推遲到一五四五年底。
自我奉獻
儘管重重障礙,改革的精神非已退到天主教世界的邊緣,而是仍然存在於教會的核心,是在煥發信徒思想的希望。與羅馬官場並肩而立的是另一個羅馬,就是老百姓,他們樂於舉行宗教慶典,卻備受庸俗和迷信的貴族輕視侮慢。很多醫院和無數的慈善機構,與城市中墮落、缺德的生活及站滿街頭的妓女並存。在這混雜的背景下,三個同伴走進羅馬。他們不是純粹過路,而是要留下來。他們在尋找未來,等待它清晰地呈現。他們不要求什麼,而是來奉獻自己。
席地而睡
依納爵預感的,向他們「關閉的門窗」,沒有應驗。雖然很多人很自私,羅馬也有善心人。三位朝聖者司鐸,一到羅馬,就有一位好心人大方地任由他們用他的房子。多年之後,這位恩人的兒子仍然記得,當他還是小孩時,父親有時會給朝聖者送食物,他們則會把食物跟比他們更窮的人分享;他也記得朝聖者們常席地而睡。
三位朝聖者到羅馬不久,就履行了他們來羅馬的原因:
把自己交在教宗手中,無條件地任他差遣。
從世界各地來羅馬的人,都是為了尋求恩惠和門路,
但是,當他們看到這幾位來自巴黎的有識之士,
投身服務,而不求任何回報,定會感到非常奇怪。
不久,教宗保祿三世派雷奈士和法伯爾在羅馬大學教書。羅馬大學建於一三零三年,曾在一五二七年羅馬遭掠奪後關閉,保祿三世當選教宗後重開。法伯爾教神學;雷奈士也嘗試教神學,但他用了一段時間才掌握到在課室授課的技巧。他說:連依納爵對他的表現也感到尷尬。他和法伯爾大概在羅馬大學教了兩年書。其實教學工作很適合這兩位曾在大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儘管教學與他們獻身的謙卑工作相距甚遠,也與團體擬定的工作不符。
依納爵最喜歡的工作
依納爵閑著,於是重拾他在此時最喜歡的工作── 與人交談 ── 當他發現某人準備好,就會鼓勵他去做他的神操。第一個做神操的是奧爾提茲博士:過去他對依納爵在巴黎的懷疑,現在消失了,並熱心追隨依納爵,忠實地支持他。他在依納爵的指導下,在卡西諾山做了四十天的神操。他稱依納爵教了他一套新神學,一套不是用來教學用的,而是應用到生活裏去的新神學。
許多人也同樣成功地做了神操,他們包括出名的錫耶納共和國大使,一位樞機的侄兒,一名醫生和康塔里尼樞機。康塔里尼樞機後來成了同伴們的重要聲援支柱。在此期間,他們的同伴郝塞斯在巴都亞去世了。這就是三位同伴初到羅馬的生活,跟他們夢想著在耶路撒冷做的,確實非常不同。一五三九年四旬期後,其他同伴來到羅馬與他們會合。他們都在意大利不同的城市,經歷了非常豐富的牧靈事業,留下一段又一段難以忘懷的情誼。這些友誼後來都成了裨益。
反省:
當他們看到這幾位來自巴黎的有識之士,投身服務,而不求任何回報,定會目瞪口呆,感到非常奇怪。
請回顧你慷慨奉獻,作自我犧牲的生活片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