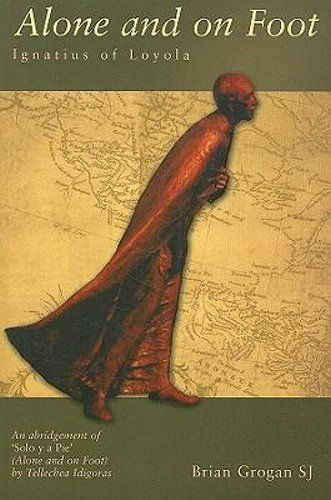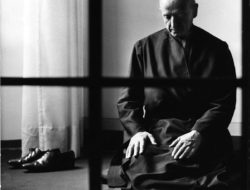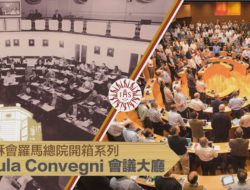第三十章:在巴黎讀書行事,1528-34年
依納爵跳舞
依納爵可以做體力要求不高,不像徒步從巴黎走到盧昂那樣驚人的壯舉,下面的小插曲揭示他複雜個性的另一面。由於過分拘謹,這個故事在一五七二年,初版官方傳記中被刪除了,兼一直被遺忘,到一九六五年才被納入。
有一個耶穌會士病得很重,鬱鬱寡歡。依納爵探望他,問他可以做什麼去驅散他的憂悶。病者說,他只想到一件可以令他感到好些的事:「如果你能像你家鄉的人那樣,給我唱唱歌跳跳舞,我想這會帶給我一點安慰」。
依納爵回答說:「這真能使你高興嗎?」
「哦,當然囉,非常高興」,病者說。
依納爵不顧自己的腿有點跛,照病人的要求做了。唱罷舞罷,他說:「請不要叫我再這樣做了,因為我不會做了」。生病的會士因依納爵的愛德而高興不已,他離開後,吞噬他心靈的憂苦消散了,病情開始好轉,不久便痊癒了。
遭同伴離棄
依納爵留在薩拉曼卡的四個同伴,沒有繼續留在他的團體,而是各走各路。依納爵在巴黎給他們寫信,保持聯繫,卻告訴他們:「他能夠把他們帶到巴黎讀書的機會微乎其微」。其中一人在墨西哥發了財;另一人返回家鄉塞戈維亞,「開始度一種似乎已忘卻先前決定要過的生活」;第三位被任命為墨西哥主教,一抵埗就慘死了;第四位做了方濟會會士。時間有助澄清與定人心的奧秘及渴望的真誠。依納爵誘人的魅力,不能保證最初的忠誠,能抵擋得住每個衝擊。沒有他的臨在,阿爾卡拉和薩拉曼卡的團體散了;在巴黎經他培育,願過神聖生活的三名大學生也離開了。這一切都沒有令依納爵放棄去繼續尋覓志同道合的良伴。
得宗教裁判所開釋
一五二九年九月,依納爵從盧昂回到巴黎,得悉圍繞三位大學生所發生的異事,導致有人向宗教裁判所投訴他。於是,他沒有等宗教裁判所傳召,便主動去見裁判官,說他知道他在找他,並表明期望配合檢察官的調查。他給檢察官提供了一切有關詳情,令後者異常驚訝。之後,他請檢察官盡快審理他的案件,好讓他放心開始新學期的大學生活,了斷與宗教裁判所的瓜葛。宗教裁判所的檢察官是個道明會會士,他承認他的確收到一份投訴,但對此不感興趣,並允許這個無畏的學生自由離去。
一五二九年十月一日,依納爵開始他在聖巴爾伯學院的文科課程。院長曾恐嚇,若他露面就會當眾鞭打他,因為他以宗教名義,犯了院規。全體學生已被召集,見證這可悲的場面。在這關鍵時刻,依納爵去見這個可怕的院長。他不介意個人受辱,但身為導師和使徒,他擔心他的追隨者不能承受這考驗。他只用了幾分鐘時間,就說服了院長改變初衷,並成了他的朋友。多年後,就是這位院長為耶穌會打開到印度傳教的大門。天主眷顧的方法多麼諷刺!
認真求學
依納爵減少了做使徒工作,認真讀書,令旁觀者詫異。有一天,一位老師冒昧地對他說,「他奇怪他可以靜靜地讀書,沒有人再來找他麻煩了」。依納爵毫不客氣地回敬:「原因是我沒有講論天主的事,只要課程一完結,我立即照舊行事」。他不愛讀書,但有成年人的韌力。哲學和神學在他心內激發敬畏,這是但凡有系統地接觸這兩門學科的人都會有的。無虛假的靈修主義永遠不可能代替這兩門學科。辛辛苦苦求學的經驗,讓他從中抽取惠及後人的實質碩果。他奉勸耶穌會修生要有學養;要認同須整合聖經、教父教理及士林學派的智慧;要感到需要有一套教學法,並賞識學術學位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須為學生提供最基本的需要,使他們能夠專心向學。
他讀書了,不過他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想成為知識分子。他散發的是活力。他不會有什麼巧妙思維令老師們驚歎,但每當談到神學,他深邃的認識,使他們震驚。
他的個性中有一股魅力,使同學甚至教授們信服。
他不是個能言會道,博得別人表面同情的口才家。可是,每到一處,他都像酵母,掀起波動,吸引別人注意,但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周邊的環境和當中的人。
反省:
你覺察到自己有什麼可以幫助別人,找到天主的天賦嗎?
(待續)
《踽踽獨行:依納爵.羅耀拉》Alone and on Foot (Ignatius of Loyola)
訂購資訊 https://is.gd/kPsA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