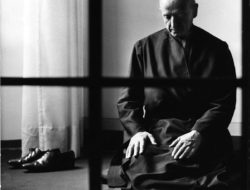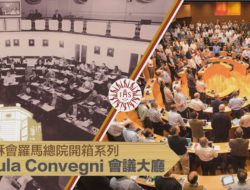施省三神父(Joseph Shih Hsing-san, S.J.)日前去世, 雖然天主教週報以及耶穌會網站都有介紹他的生平,但是在台灣認識他的人很少, 可是他在中華耶穌會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這幾天看到教會對他的生平介紹,從大陸到菲律賓晉鐸, 後來到梵蒂崗在教廷額我略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及天主教傳教史,後來到梵蒂崗電台負責中文廣播, 一直到退休為止。
只是, 他的一生服務教廷, 卻有一項很大的貢獻卻幾乎沒有人提到,那就是他在西方漢學界,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天主教研究史上有很獨特的貢獻, 原來近年來在學界及政治社會界都在鼓吹利瑪竇促進中西文化及宗教交流的角色及貢獻,事實上, 最早帶利瑪竇入華的是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他和利瑪竇一起奠定了天主教傳教士入華的基礎, 也被稱為西方第一位漢學家,只是因為他比較多使用佛教的術語來介紹天主教, 利瑪竇後來建議他回羅馬述職,結果中華教務就由利氏接管主持。
利氏的路線,眾所週知,就是從中國古代儒家切入,來介紹教會,與羅氏路線不同, 事實上, 羅返回歐洲, 帶回去不少做到一半的工作, 以及許多文獻地圖,他先到西班牙, 晉見國王,呈獻不少禮物,也帶回頗多訊息,後來又回到故鄉意大利,並且晉見教宗,也獻上許多與中國有關的禮物及訊息,雖然他還想回中國,但終究沒有回去,而他所攜回的許多東西一直被埋沒多年。
施省三神父在教廷因地利之便,梵蒂岡各圖書館以及各修會的檔案館多在附近,開始研究羅明堅, 發表了羅明堅的研究論文,打破了多年來學界多以研究利瑪竇來主導中西交流史的局面,羅明堅的研究漸漸受到重視,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張西平教授首先在大陸的《歷史研究》上發表對羅明堅神父的研究,稱讚羅乃歐洲漢學家的第一人,後來陸陸續續因為台灣利氏學社出版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以及徐家匯圖書館教會史文獻,羅明堅的研究資料增加不少,許多學者也開始注意到羅明堅,我也在這潮流下,研究羅明堅的《天主聖教實錄》而發現了被忽視了四百多年的「天主」最早的中文名稱「了無私」。
羅神父帶回歐洲的地圖以及中國經典的翻譯也都有人在研究當中,研究羅明堅成為相當熱門的項目,這種趨勢不得不歸功於施神父。可惜因為施神父為學界所知的是他的西文名字Joseph Shih Hsing-san, 在被譯成中文時就往往連姓都被翻譯錯了。
研究羅明堅的文章往往會提到施神父的開拓性研究,但是他的名字卻變成了發音近似的他名。我在1988年在比利時魯汶初識施神父, 當時韓德力神父的南懷仁基金會紀念南懷仁去世三百週年紀念,舉行了一次中華天主教史國際學術會議,施神父應邀參加, 並撰寫了一篇南懷仁的宗教著作的論文,我也提出一篇論述夾在朝廷與教會之間的南懷仁,會議中受到施神父的鼓勵,印象深刻。
我告訴他在會後要去義大利羅馬獨自去朝聖, 他立刻從口袋中捣出一張羅馬的公交車回數卡送給我使用, 這使我的羅馬之行方便許多。那次開會是借用一座舊的修道院, 會議廳旁還有一間小房間明供聖體,供與會的神職及教友使用,有一次我與他外出返回會議場地時, 他就先去朝拜聖體,才回到宿舍,虔誠慎獨的行為, 令人欽佩。
那次會後, 斷斷續續與施神父偶有聯絡,多半是他從羅馬回中國或返回羅馬途中,經過台北時見到的,他在台北時總是住在耕莘, 與會士們相聚, 尤其是上海的神父們。我總在主日彌撒時見到他低調參與, 坐在教友群中, 謙虛和善, 看不出來他是一位大學者,也是教廷裏做過大事的人物。
記得大概是1997年年底,台北的利氏學社召開年度會議, 施神父也參加了,會議當天早上由輔仁大學張奉箴神父報告, 由我評論, 可是張神父剛剛講到一半,突然對著旁邊的我說了一聲對不起,就昏厥倒地不起, 與會人士慌成一團, 在叫救護車時,賴甘霖神父及趙儀文神父為張神父急救,只見施神父從懷中拿出一個小本子為張神父念赦罪經,為張神父完成了終傅,可見施神父他的日常修為, 隨時準備好為世人服務, 作好一位神職的工作。
我覺得他是一位很標準的耶穌會士,為修會提供了很正面的形象。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許多人四散分離, 不能相見, 施神父也在此疫情中去世, 許多人不能送他最後一程, 令人遺憾, 但是施省三神在學術界以及他在人世間的作為, 將令人懷念, 耶穌會中華會省將來為會士們寫小傳時,也不要忘記施神父在這方面的貢獻及芳表。
(作者:古偉瀛 台大歷史系 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