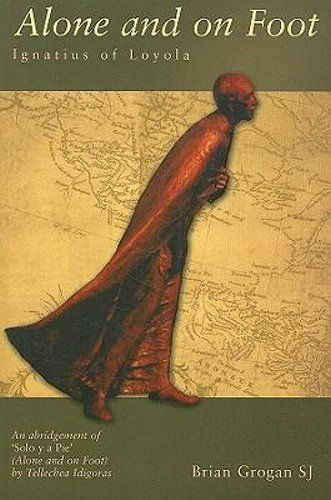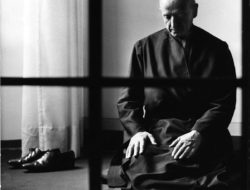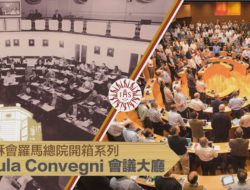第四十六章:「我要在羅馬恩待你」,1537年
被安置與聖子在一起
依納爵死後,翻閱他私人物品的人,在他的筆記中,發現這句重要的話:「當天父把我和祂的聖子安置在一起時」。很明顯,指的拉斯多達,雖然這片語本身不怎樣富啟示性。依納爵不是那種硬要折磨自己去表達那被定義為不能表達的神秘者,卻把烙印默存心中。
他在那個時期有大量豐富的神視,而拉斯多達的神視屬於這時期的最後階段。這時期包括他在一五三七年初所做的大避靜。一五三七年為他來說,實在太漫長了,隨著日子的流逝,就是他對未來的希望。依納爵一直都把即使是最微小的事,看作是天賜的人,因此,要他忘記在耶路撒冷度餘生的計劃,使他陷入完全摸不著頭腦的境地。
「我要在羅馬恩待你」;「我」是基督自己,是他夢想在耶路撒冷尋求的;「我要恩待」,基督將會恩待;「你」,指的是同伴們 ── 不只依納爵一人 ── 整個團體是這個令人安心的許諾的對象;「在羅馬」,方向由耶路撒冷逆轉,指向羅馬。打從他們在巴黎的時日開始,羅馬就已經是同伴們的另一個計劃,假如去聖地的計劃受阻。
羅馬,很壯麗……
拉斯多達的神視,使朝聖者依納爵相信他正朝著正確的方向走;然而,這條路充滿許多不明朗因素。他有一種預感:困難、考驗和迫害 ── 簡言之,敵意 ── 在羅馬等著他們。他將這種預感描繪為:他看到在前面「關著的門窗」。堅定相信及明確擔保,並不等於萬里無雲,前景一片明朗,看得清楚透徹。他唯一的選擇是繼續行。依納爵、法伯爾和雷奈士,在一五三七年秋天到了羅馬。
羅馬當時的情況很複雜,無數的教堂、宏偉的宮殿、浮誇的紀念館紀念碑等等,高高聳立在平民百姓簡陋住所的中央。儘管意大利被外國勢力壓得喘不過氣,儘管羅馬慘遭新教攻擊,影響力在歐洲許多地方都已經式微,文藝復興的精神活力仍然興旺。藝術和文學仍在蓬勃發展,人口也持續增多。羅馬,的確不同凡響。新貴挑戰顯赫家族的權力和影響力,築新宮殿新別墅來較量一番,炫耀賣弄。在未盡全毀的古老遺蹟、在無數的教堂、在奪目的噴泉、在剛發掘出來的地下墓穴,異教徒和基督徒昔日的輝煌,仍有蹟可尋。
……但很腐敗
駐教廷的樞機,同他們龐大的隨從和親信,不僅掌管天主教界,更在每次閉門會議選新教宗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強國的大使給羅馬帶來世界脈搏,亦在炫耀自己,務要躋身於形形式式的辯論,為自己所代表的國王和王子爭光。數以百計的大學學者和神職人員,紛紛由歐洲各地湧到羅馬,想在教廷謀得一官半職,或在這個樞機或那個主教那裏覓得住所、職位或俸祿。
始自阿法翁時期的教宗,羅馬就是一個巨型的職務任命代辦,是個勾心鬥角,充滿野心、貪婪和賄賂的城市。錢財可以打開任何一道大門,一切都可以買賣,顧不得教廷收入的真正目的是為提供牧靈服務。買賣教會職務成了教會一大禍根,也是最惡劣的。在眾多濫權行為當中,常見的是特權獨享;亂設職位,使很多職位有名無實;買賣教區和堂區。當代道明會一位倫理學家把當時教會的情況形容為「秩序大亂」。
革新教會?
一代接一代的革命家大聲疾呼,要從根本上剷除這些罪行,結果他們的控訴不是消失得無形無蹤,就被徹底肅清。教廷太想維持現狀,不會支持任何嚴肅改革。人們仍清楚記得一五二七年羅馬慘遭外來軍隊洗劫蹂躪,教宗被關進聖天使堡。所以,不會願意見到任何外來勢力干涉羅馬內政。被掠劫的那段可怕時期,不乏認為是天主在懲罰這個所謂「聖城」的傳道人和先知。亦有人預言 ── 或許只是表達他們的渴望 ── 會有一位像似天使,由上天派遣的教宗出現,糾正劣勢,袪除一切罪惡。
反省:
羅馬是個勾心鬥角,充滿野心、貪婪和賄賂的城市。錢財可以打開任何一道大門,一切都可以買賣。
你如何將當今教會跟十六世紀的教會作一比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