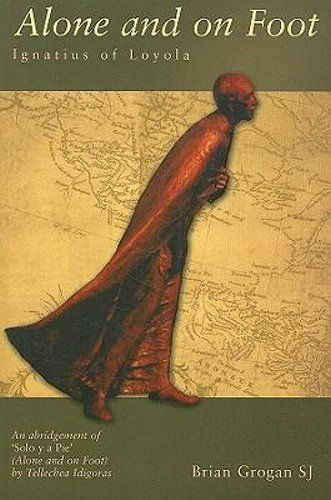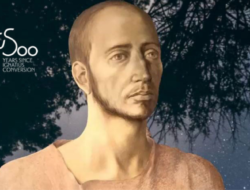第十二章:離開羅耀拉,1522年2月
割斷家族關係
為了去耶路撒冷,依納爵要割斷親情,但他沒有讓人知道這在他心裏醞釀的計劃。
他大概是在一五二二年二月離開羅耀拉府邸的。脫離家族關係帶來個人、家族和社會各層面上難以估計的影響。依納爵自己感到有信心和自由,但他害怕家人的反應,特別是他哥哥馬爾定,因為哥哥是他監護人,是一家之主。
只有這一次,無畏的依納爵沒有與家人正面衝突;他尋找離家的藉口。他向哥哥暗示,他想去那瓦勒拜訪他以前的施主納寨拉公爵,因為公爵已知道他痊癒了。但哥哥馬爾定看穿內情,「他領依納爵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嚴肅地用盡好話,請求他不要再做傻事,要想想家人對他的期望,也要看看自己在哪方面能有所作為,還說了其他類似的話,都是為了使依納爵放棄他的好志願」。
他的家人擬說服他想他們所想,使人聯想到祁克果有趣的比喻:被鴨子馴養的小鷹。「依納爵給予的答覆是,只要不放棄他堅守的真理,他避免與哥哥爭論」。
皈依的熱情
依納爵為遠行作準備,裝作要在他的保護人公爵家裏安頓下來的樣子。他整頓行裝,衣著華麗,也沒有忘記把劍和匕首插在腰間的皮帶。一個心細的人會注意到依納爵看周圍的人的樣子,因為要向身邊的人道別或永別,看著一張張心愛的面孔,總難掩依戀的眼神。
他的意志現在更加堅強,他皈依的熱情給他的人生指出了一個新方向。「因而,依納爵騎著一匹騾子」,於一五二二年二月離開羅耀拉府邸。他曾意氣風發,旁若無人,策馬馳騖到潘普洛納歷險;現在,他平和地坐在騾背上,展開新的歷驗,至於將來怎樣,尚未明確。
生活中不可預見的結果,往往隱藏在小小的但經過深思熟慮而選擇的行動背後。
依納爵在兩個家僕的陪伴下出發了。這兩個家僕是家人指派的,為了確保依納爵安全到達目的地。他的哥哥伯多祿,以後會成為離羅耀拉堡很近的阿茲柏提亞鎮的本堂神父,也一道同行。伯多祿是依納爵在一五一五年犯事的同夥,在這次歷史性的行程前幾個月,他成了一個女兒的父親。對依納爵來說,這個哥哥是他所認識的最親、最具體的「教會人士」。
在亞蘭匝宿守夜
以平信徒身分,依納爵說服了他的神父哥哥,「在亞蘭匝宿的聖母小教堂守夜」。他們爬到建在陡峭巖崖的小隱修院,依納爵熱切祈禱,為他的行程增添了力量。
許多年後,依納爵回憶他從這次守夜中的得益。那晚,他在漆黑中,一直守夜至天亮。之後,他們下到他們一個姐姐家裏,伯多祿便留在那裏。依納爵在潘普洛納受傷後,也曾在這位姐姐瑪達肋納家中住過幾天。
依納爵與哥哥在這裏道別,從此兩兄弟之間的距離日漸擴大,伯多祿對依納爵的冷漠與敵對態度,與日俱增。兩兄弟此後再沒有見面了。一五二九年,伯多祿死在從羅馬返家的途中;他多次往返羅馬,為起訴他家鄉聖嘉勒隱修會的修女。
貞潔願
依納爵以慷慨的心神在聖堂裏守夜,這使他不但重新得力,更使他開始擺脫一直纏繞他的衝動。看來,他大概是在亞蘭匝宿發了貞潔願。多年後,他承認這個事實。
「由於他擔心貞操比其他方面更易受到攻擊而失足,所以當他還在途中,便在他特別敬禮的聖母前發了貞潔願」。
雷奈士為此作證:「在此以前,他雖常被慾念擊敗,但從那一刻開始直到現在,我們的主給了他貞潔的恩賜,而我相信,這使他近乎完美」。為使他的貞潔誓願不至淪為花言巧語,「從離開家鄉那一天起,他每天晚上都打小苦鞭」。
處理債務
大概是因為他不想撒謊,依納爵接著便去了那瓦勒。他在那裏應該沒有見到公爵本人。儘管他已下定決心棄絕世俗財物,他還是要求償還欠他的薪金。當時銀庫財根短缺,但公爵說「即使他在各方面都缺錢,也不會欠羅耀拉一文」,甚至準備讓依納爵管理他一項優質產業,「以肯定他在過往贏得的聲譽」。
依納爵無心管理任何產業或人,只想做自己不可預測的冒險之旅的主人翁。他拿了錢,要求把一部分還給他尚在拖欠的人家,其餘的則用來復修一尊聖母像。
獨行
依納爵向陪伴他的僕人透露,他要「以一個貧窮懺悔的朝聖者」身分去鋸山,並打發他們走。這是他家人在之後的十三年裏,得悉有關他的最後行蹤;直到一五三五年,他匆匆回了羅耀拉一趟。假如他願意的話,他大可重投上流社會的舒適生活,美好的將來為他敞開大門。
但他追隨了自己獨個兒的行徑,一條由他自己選擇的道路。
反省:請回顧一下你自己獨自作出的決定性選擇
(待續)
《踽踽獨行:依納爵.羅耀拉》Alone and on Foot (Ignatius of Loyola)
訂購資訊 https://is.gd/kPsA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