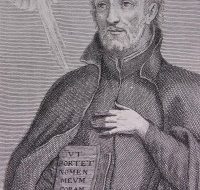身為阿根廷的耶穌會士,於1969年被祝聖,豪爾赫•馬里奧•伯格里奧發現自己身在這些動盪當中。
1970年代在阿根廷爆發的「骯髒戰爭」,超越國家的暴力也威脅到許多神父,特別是耶穌會士- 甚至當政權增選多位聖統中人。伯格里奧在36歲時,受命為阿根廷耶穌會的長上,被推入即使是最有經驗的領導人都飽受試煉的內外混亂情況。
「我不得不處理困難的情況,而我都是突然、自己決定事情。」方濟各去年說,承認他「做決定的威權和快速方式讓我有嚴重的問題,並被指責是極端保守。」
伯格里奧完全接受耶穌會捍衛窮人的激進轉向,雖然他被視為解放神學的敵人。批評者貼他標籤﹐稱他是阿根廷軍政府的合作者,即使傳記顯示,他工作認真、審慎,以挽救許多人的生命。
這些都沒有結束耶穌會內反對伯格里奧的勾心鬥角,而在1990年代初,他實質上是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被流放到一個邊遠的城市。
但是在經典的耶穌會的傳統,伯格里奧順應了修會的要求,並設法在這一切中找到天主的旨意。矛盾的是,他來自耶穌會的虛擬疏離,鼓勵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樞機主教Antonio Quarracino於1992年任命伯格里奧擔任助理主教。「也許一個壞耶穌會士可以當一個好主教」當時一位阿根廷耶穌會士說。
1998年伯格里奧繼位Quarracino為總主教。2001年,若望保祿任命伯格里奧為樞機,是樞機團120位樞機中僅有的兩位耶穌會士之一。
他在聖統中的爬升,卻好像在鞏固他在耶穌會中對手對他的懷疑。
因此當伯格里奧在2013年3月被選為教宗,你幾乎可以聽到全世界的耶穌會團體集體發出的噓聲。
「事實是他在內部已經有點被耶穌會拒絕,若非如此,他可能不會成為主教。」溫貝托•米格爾•亞涅斯神父表示。他跟方濟各一樣是阿根廷耶穌會士,負責羅馬格里高利大學的道德神學系 – 這所耶穌會學校有時也被稱為「教宗的哈佛」。
而如果伯格里奧沒被選任主教,他不會變成樞機,最終,成為教宗,因為傳統上樞機團從同階級中選擇聖伯多祿的繼承人。
亞涅斯引用了聖經著名的經句打趣說:「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當然現在,方濟是「弟兄中的弟兄」,正如現任耶穌會總會長倪勝民神父所說。
「我的印象是,他藉著每天的講道和教理,好像在和整個教會作一種依納爵式的避靜。」澳洲籍樞機主教最近說。
方濟各知道教會有些角落依然對耶穌會十分不滿,特別是在梵蒂岡,但他並沒有因此改變他的風格。他規避了常用的禮節,推崇一位依納爵最初的同伴,彼得•法伯爾。方濟各曾稱讚他「與所有的人對話,即使是在最偏遠的人,甚至是與他的對手。」
他生活簡樸,拒絕了傳統教宗的寓所,住進梵諦岡客房裡的一個小團體。他也強力鼓吹,其他神職人員,尤其位居高階者,應該迴避他們職權的福利和特權。
耶穌會對方濟各的影響延伸至他治理的模式。他當教宗的首要行動之一是,任命來自全世界的八位樞機主教組成諮議會 – 他們沒人出自功能失調的羅馬教廷 – 像個廚房內閣,很像耶穌會長上們工作的方式。他也使用了類似的模式處理具體的任務,如整頓梵蒂岡的財政。
這是一種分辨 – 行動之前先聆聽並默想 – 是依納爵靈修的一項基本德行,也是方濟各致力「改造」教宗權及整個教會的核心。
但這也意味著,很難精準地說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方濟各曾一再讚揚耶穌會士「神聖狡猾」的特色 – 即基督徒應該如耶穌所說「明智如蛇,但純樸如鴿」。但教宗的開放也是他耶穌會培育和發展的標記,意思是說,連他都無法肯定,聖神要領我們前往何處。
「我承認,因為我的性格,通常我想到的第一個答案都是錯的。」方濟各在2010年一次訪談中說。
「我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我甚至沒有所有的問題。我一直想到新的問題,而新的問題不斷冒出來。」
作者/David Gibson
本文轉載自宗教新聞社,版權均為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