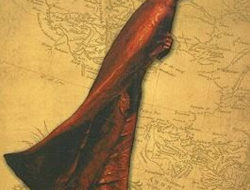五月十一日是利瑪竇(Matteo Ricci)神父逝世四百一十周年紀念,這位傳奇的耶穌會士生於一五五二年,卒於一六一零年。
他的生平和在中國傳教的方法,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也是學術研究的熱門課題。特別是過幾年,台北、巴黎和三藩市均舉辦了國際會議,探討他的影響和意義。
利氏不僅開創新穎的傳教方法,也提出西方社會與中國接觸的嶄新方式,其成功的魅力遠遠延伸至天主教圈子之外。
利瑪竇在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去世之年誕生,但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路。他為甚麼不單純重複沙勿略的做法,起碼可以贏得在亞洲各地為幾萬以至數十萬人付洗之讚譽?
這條路從何而來?利瑪竇在意大利時的初學導師及後來出去傳教時的長上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神父挑選了他和其他幾個人,在亞洲開創完全不同的傳教方法:傳揚印度人的天主教、日本人的天主教、中國人的天主教。
為此,傳教士必須:走進福傳對象的思想與內心、語言與文化、符號與情感,才能重新演繹天主的臨在、耶穌和教會生活的意義。利瑪竇是當中佼佼者,最能實現這種傳教方法。
是甚麼因素觸發這次大膽的嘗試,背離了傳教士將基督信仰與歐洲文化連在一起的傳統做法?
范禮安的創造力無疑是必要的,他的想法超越了歐洲文化的囿限。而利瑪竇的經營能力和語言天份,則使他從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物,變成名震全球的名人。
另一因素也許是利瑪竇抵達中國的機遇:葡萄牙一度劃出強有力的版圖,但他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經葡國殖民地澳門進入中國大陸時,正值葡國殖民主義的衰落。

一五八零至一六四零年間,葡萄牙被西班牙吞併,完全喪失了擴展中的殖民帝國的風采和積極性,對殖民地的管治相繼瓦解,在亞洲及中國作為主要殖民大國的年代結束了。利瑪竇這個時候跟亞洲和中國接觸,既沒有背負殖民者的包袱,也不會因歐洲人身分而樹敵。
葡萄牙人身為殖民主義者,固然不獲好評。沙勿略於一五四零年代出訪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時,對葡萄牙人的行徑感到震驚,覺得有損福傳工作,因為福傳是要把福音精神體現出來。因此,他向前進發。
葡萄牙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均承認傳揚福音是其事業一部分(亦是為了把歐洲文化強加於福傳對象身上)。沙勿略赴亞洲傳教,與其說是由教宗委派,不如說葡萄牙國王向耶穌會會祖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Loyola)提出私人請求後,便有人從歐洲出發了。
利瑪竇卻不然。一五八二年葡萄牙成了強弩之末,他此時進入中國,往績清白,沒有被那些關係所拖累,得以逐步接觸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最後抵達朝廷。
利瑪竇的影響深遠,當中他塑造的傳教方法之背景及前提,為今天再切合不過。過去六十年來,亞洲從政治及文化上向歐洲認同的包袱中釋放出來,基督宗教處於合適的位置,在中國、越南和印度進一步發展范禮安的夢想,以及利瑪竇及同伴的傳教方法:基督信仰和教會生活是「印度人的天主教、日本人的天主教、中國人的天主教」。
────────────
耶穌會士利偉豪(Michael Kelly)神父撰文。利神父2008-2018年間出任《天亞社》總編輯。1982年至今,他曾從事電台和電視製作,並為澳洲及亞洲許多宗教或非宗教刊物撰文。2018年後爲「十字架報」(La Croix International) 及 耶穌會期刊 La Civilta Cattolica 發行人。



![《植物情懷》, [法]馬克·讓松 夏洛特·福夫 著,戴捷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https://www.amdgchinese.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植物情懷》-法馬克·讓松-夏洛特·福夫-著,戴捷-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1-250x1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