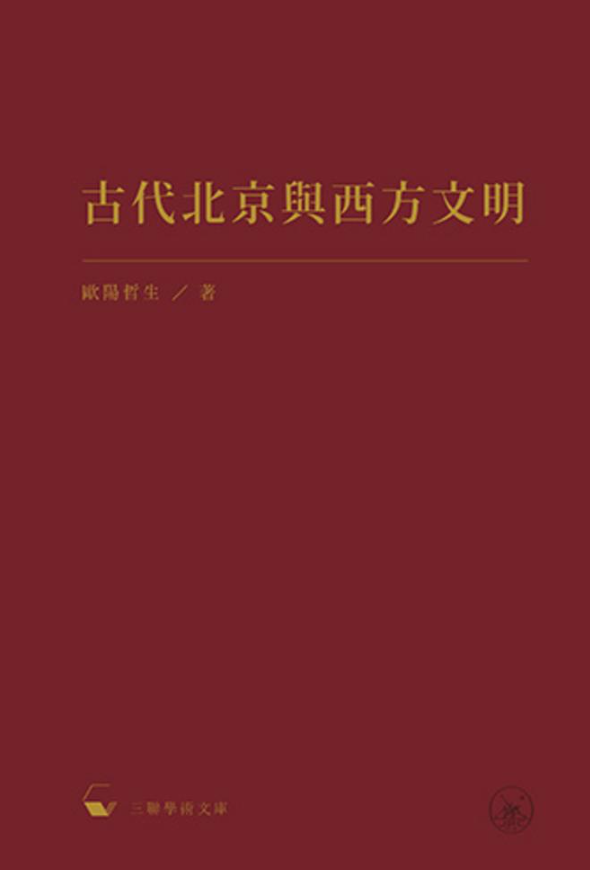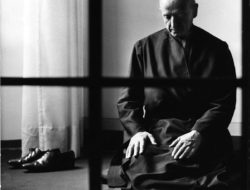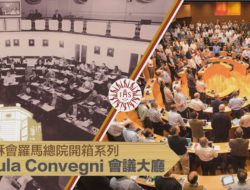早在康熙晚年,因喜愛西方琺琅工藝,馬國賢、倪天爵等人就被召進宮傳授。1716年馬國賢在信中寫道:「皇上被我們歐洲的琺琅所折服,希望其皇家作坊引入這一工藝……如今令郎世寧和我在釉面上畫圖,我們兩人如囚徒般被日夜關在皇家作坊,周圍是一群貪污腐敗之徒,我們聲稱不懂這門藝術而拒絕他們的要求。」法國耶穌會士與意大利傳教士對中方要求的態度不一樣,他們採取了與清朝合作的態度,以便進一步擴大法國耶穌會士的影響,倪天爵將這項技術帶入清宮,其工藝直接來自法國的利摩日(Limoges),1720年馮秉正的一封信提及此事:「事實上,御旨之下,中國的工匠製作琺琅的時間也不過五六年,然而其進步速度驚人,倪天爵神父仍然是他們的師傅。」

乾隆對歐洲工藝的喜愛不讓康熙,他在位期間出入清宮的西人往往是一些具有工匠技藝的耶穌會士。1780年10月15日,方守義在一封書簡中談到進宮的三種主要才能:畫家、鐘錶匠、機械師。此外就是翻譯和天文學。乾隆對西方美術和天文學極為傾慕,在外人面前也毫不掩飾,韓國英對此印象深刻:「這位君主對歐洲人過獎了,他公開對所有人說只有歐洲人才精通天文學和繪畫,中國人在他們面前只是『後生小輩』。您很容易感覺到,這種偏愛對於一個驕傲的民族該是多大的傷害,因為在這個民族眼裡,一切非出本土之物均是粗俗的。」
以畫師身份進入清宮的傳教士有郎世寧、馬國賢、王致誠、艾啟蒙、賀清泰、安德義、潘廷章諸人,王致誠在其書簡中談到他作為畫師在宮中的具體工作情形:
「在皇帝的宮殿及其園林中,除了上朝之外,他很少將王公和部院大臣等權貴們領入其中。在此的所有西洋人中,只有畫師和鐘錶匠們才准許進入所有地方,這是由於其職業而必須的。我們平時繪畫的地方,便是我向您講到的這些小宮殿之一。皇帝幾乎每天都前往那裡巡視我們的工作,以至於我們無法離席而出,更不能走得太遠,除非是那裡需要繪畫的東西是能搬動的原物。他們雖然將我們帶到了那裡,卻又由太監們嚴密看押。我們必須步履匆匆地行走,無聲無息,以腳尖著地,就如同偷著前去辦壞事一般。我正是以這種辦法在那裡親眼目睹和瀏覽了整個漂亮的御園,並且進入過所有套房。……白天,我們置身於園林之中,並在那裡由皇帝供應晚餐。為了過夜,我們到達一座相當大的城市或者是一個鎮子,我們在距皇室很近的地方購置了一幢房子。當皇帝還駕京師時,我們也隨駕返回。此時我們白天便留在皇宮深苑之中,晚上則返回我們的教堂。」

1754年10月17日錢德明在致德・拉・圖爾(de la Tour)神父的長信中,報告了王致誠在宮中服侍乾隆的情況,包括被皇帝召到熱河,在乾隆平定準噶爾叛亂後為乾隆製作《得勝圖》,皇帝要封王致誠為官,遭到王致誠的婉言謝絕,以及王在宮中向大臣們介紹法國情況,並與其他傳教士作畫和製作報更自鳴鐘、噴射水柱、玻璃器皿和自動行走的獅子等具體情形。
王致誠存世的畫作數量雖少於郎世寧,但其畫藝卻不遜於郎氏,在當時與郎氏齊名。在入宮服務的西人工匠中,蔣友仁、韓國英較為突出,他們主持了圓明園中的歐式宮殿設計。蔣友仁在1767年11月16日致信巴比甬・道代羅什,交代他是1745年奉乾隆之命,作為數學家來到北京。兩年後「應皇帝陛下之詔負責水法建設」,以為美麗的圓明園增添新的亮點:
「就是在這些花園中,皇帝要建一座歐式的宮殿,從內部到外觀都裝飾成歐洲風格的。他將水法建設交我領導,儘管我在這方面的低能已暴露無遺。除了水法建設,我還負責在地理、天文和物理方面的其他工作。看到皇帝陛下對這一切饒有興致,我利用餘暇為他繪製了一幅12法尺半長6法尺半高的世界地圖。我還附加了一份關於地球和天體的說明,內容涉及地球和其他星球新發現的運行軌跡,彗星的軌跡(人們希望最終能夠準確預測它們的回歸)。」
蔣友仁曾就其在宮中與乾隆接觸的情形於1773年11月、12月間連續三次致信嘉類思神父。第一封信談及新來的李俊賢、潘廷章兩人向乾隆進貢的望遠鏡等禮品,潘廷章為乾隆作畫像,宮中的建築風格和各種飾物。第二封信記錄了蔣友仁與乾隆的談話,內容涉及歐洲如何選擇傳教士來華、銅版畫《得勝圖》的製版、歐洲各國及東南亞、日本各地情況、當前在華傳教士情況和天體運行、皇子們的學習等。

第三封信匯報與乾隆談及天體運行、望遠鏡、宗教和傳教士的工作,對晁俊秀的評價,葡萄酒和傳教士的宗教生活等。其中在談話開始蔣友仁向乾隆介紹了「太陽中心說」,這可能是中國人首次接觸這一原理。
1774年10月23日,蔣友仁不堪工作勞累和耶穌會被解散消息的打擊倒下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耶穌會士在報告他去世的噩耗時,對他在華的工作成績,特別是在圓明園建造水法、噴泉和西洋樓的過程作了詳細回顧,最後總結道:
「如人們有朝一日撰寫中國教會年鑒,甚至只需引證非基督教徒對蔣友仁神父的說法和想法便可讓後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於其才華。皇帝為他的葬禮出了一百兩銀子,還詳細詢問了他最後的病情,最終道:『這是個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這些話是很高的讚揚,若這些話指的是一個韃靼人或中國(漢)人,它們將使其子孫後代享有盛譽。」
韓國英在京二十年(1760-1780),據一位與他關係密切的在京耶穌會士回憶,他「關注、愛好各門學科,擁有豐富的學識;其專心尤其是其熱忱使他在從事的所有工作(如天文學、機械學、語言歷史研究等)中均獲得了成功。」「他為北京的傳教士們寄往歐洲並在國務大臣貝爾坦(Bertin)先生關心支持下出版的學術論文做了大量工作,但他從不希望這些著作署他的姓名。」

1764年11月7日韓國英致信德爾維耶(Dervillé)神父透露:「我在皇宮裡工作了四年之久。在皇宮裡做了一座配有噴射的水柱,鳥的鳴叫聲和變幻不停的動物形象的大水鐘。我經常見到皇帝。請您相信我,他只讓那些違抗其旨意的人成為殉難者。如果沒他公開地保護我們,我們很快就會不在人世。請您為很喜歡我們的皇帝本人及其全家的歸信祈禱吧。」又據其1767年11月22日書簡稱:「余在中國離宮御園之中,前為噴水匠與機匠凡五年,自皇帝建立武功以後,又成園藝師與花匠。」韓國英逝世後留下的遺著多收入《中國叢刊》。
註釋:
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6) 義大利人,耶穌會士,於西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來華,為首批隸屬於傳信部來華的傳教士。隨之北上京師在宮中供職,擅長繪畫、雕刻,很得康熙皇帝的賞識。
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中國的宮廷畫家將承德避暑山莊中的山光水色繪成三十六景,由馬國賢根據原畫刻製成銅版,印出了一套《御製避暑山莊圖泳三十六景》(《熱河三十六景圖》)的銅版畫。馬國賢后來還與其他的歐洲傳教士共同以銅版印製了《皇輿全覽圖》,這是中國地理史上第一部有經緯線的全國地圖。此後,馬國賢共鐫刻中國地圖44幅,並應康熙之邀, 將雕刻銅版技術傳授給中國人。這是銅凹版印刷術最早傳入中國的情況。馬國賢於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回國。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原名朱塞佩·伽斯底裏奧內,聖名若瑟,義大利人,耶穌會士、畫家。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來中國傳教,隨即入皇宮任宮廷畫家,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國從事繪畫50多年,並參加了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工作,為清代宮廷十大畫家之一。郎世寧擅繪駿馬、人物肖像、花卉走獸,風格上強調將西方繪畫手法與傳統中國筆墨相融合,受到皇帝的喜愛,也極大地影響了康熙之後的清代宮廷繪畫和審美趣味。其主要作品有《十駿犬圖》《百駿圖》《乾隆大閲圖》《瑞谷圖》《花鳥圖》《百子圖》《聚瑞圖》《仙萼長春圖冊》《心寫治平圖》(《乾隆帝后妃嬪圖卷》)等。
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 法國人,耶穌會士,自幼學畫於里昂,後留學羅馬。工油畫人物肖像。
西元1738年(乾隆三年)來華,獻《三王來朝耶穌圖》,乾隆時受召供奉內廷。初繪西畫,然不為清帝所欣賞,後學中國繪畫技法,參酌中西畫法,別立中西折中之新體,曲盡帝意,乃得重視。與郎世寧、艾啓蒙、安德義合稱四洋畫家,形成新體畫風。
艾啓蒙(Ignatius Sichelbart,1708—1780),字醒庵,生於波西米亞(今屬捷克),耶穌會士,1745年(乾隆十年)來中國,師從郎世寧學畫,得郎氏指授,使西法中用,很快受到清廷重視,詔入內廷供奉。
他擅長人物、走獸、翎毛類繪畫,與郎世寧、王致誠、安德義被人稱為四洋畫家,形成新體畫風。他已知的作品有紫光閣武功圖中《準噶爾戰功圖》(1755年,乾隆廿年);孝聖皇后八旬萬壽(1771年,乾隆卅六年),《香山九老圖》,著錄於《國朝院畫錄》;《十駿圖》(1772年,乾隆卅七年)。《寶吉騮圖》軸(1773年,乾隆卅八年),絹本,設色,藏於台北故宮。
賀清泰(Giuseppe Panzi, 1734-1812),原名Louis Poirot,法國人,耶穌會士,曾經留學意大利,精通天文學、數學,於公元1770年(乾隆卅五年)來華,不久便進入宮廷供職。
潘廷章擅長作油畫肖像,曾為乾隆皇帝繪製油畫肖像。他在公元1773年(乾隆卅八年)畫的《達尼厄樂先知拜神圖》受到蔣友仁的推崇,認為精妙不在郎世寧之下。存世作品極少,現所見到的僅有半幅,即故宮博物院藏《廓爾喀貢馬象圖》卷,是其與賀清泰兩人合繪,後面所繪兩匹馬,是現知潘廷章的唯一真跡。
賀清泰與《古新聖經殘稿》文言文之外,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也常以白話文著譯,而其集大成者,非屬乾嘉年間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中譯的《古新聖經》殘稿不可。《古新聖經》之所以為“殘稿”,因賀清泰並未如數譯畢武加大本《聖經》(The Vulgate Bible)七十二卷。生前,他僅譯得卅七卷,但已達一百萬餘言。雖然如此,賀清泰仍為所譯寫了兩篇序言,而且是北京土語與北京官話混而用之,書序史上罕見。第二篇序言中,賀氏引述了聖熱落尼莫(St. Hieronymus or St. Jerome, c. 347-420)因好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前106-前43)華美的文體(style)而在夢中為天主座下的天神鞭苔的歷史名典,將之附會到《聖經》中譯去,堅信唯有用乾嘉時代的北京俗語譯經,方能顯現天主託人寫經的本意。因此《古新聖經》用北京俗語中譯,可謂天主教“有意”用白話書寫最明顯的例子,也是《聖經》首度以中國通俗之語翻譯的首例,可視為清末以前最重要的白話文書寫成果,而且還是胡適所謂“有意”為之的白話文書寫成果。
蔣友仁(P. Benoist Michel),字德翊,原名伯努瓦·米歇爾,1715年10月8日出生於法國歐坦,於1774年10月23日逝世,法國耶穌會士、法國傳教士,天文學、地理學、建築學家。
公元1743年(乾隆九年)抵澳門,經欽天監監正戴進賢推薦奉召進京。入京後,埋頭學習滿、漢語言文化、孔孟經典、哲學、歷史等中國傳統文化,1747年才委令他辦事。他不僅精於建築設計,而且又熟諳鑄造技術。曾參與圓明園的若干建築物的設計。他在《皇輿全覽圖》基礎上,增加新疆、西藏測繪新資料,編製成一部新圖集《乾隆十三排地圖》(乾隆內府輿圖),最終完成了我國實測地圖的編制。著有《坤輿全圖》、《新制渾天儀》等書。他還曾譯過《書經》、《孟子》,譯拉丁文《書經》十分審慎,其瞭解漢文之深,與譯筆之忠實,遠出以前各譯本之上。
韓國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 法國人,耶穌會士,其所翻譯的《孝經》全文法譯本 “Hiao-King, ou Livre Canonique sur la Piété filiale”(1779) 是目前確認的近代歐洲早期五種《孝經》譯本之一。
此譯本收在其名下之《中國古今孝道》(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一書中出版。
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法國人,耶穌會士,1750年抵華,1754年錢德明發願研究中華文化,他的許多作品讓西方世界更加瞭解了遠東地區的思想與生活。
他撰寫的一本滿語辭典《韃靼語-滿語-法語辭典》於1789年出版於巴黎,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作品。1772年,他將《孫子兵法》翻譯成法文,這本書在軍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其他著作主要記錄在《中國歷史、科學與藝術回憶錄》(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共15卷),其第12卷〈孔子傳〉(Vie de Confucius)比在華傳教士先輩們整理得更準確、完整。
白晉(Joachim Bouvet,1656年-1730年) 法國人,耶穌會士,一作白進,字明遠。1678年加入耶穌會,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選派出使中國傳教,出發前被授予「國王數學家」稱號,入法國科學院為院士。同行者有:洪若翰、劉應、塔夏爾、李明和張誠。
1685年3月3日,使團自布雷斯特起航,途經暹羅時,塔夏爾被暹羅國王留用。其餘五人於1687年(康熙廿六年)抵達浙江寧波。因海禁未開,洋人不能深入內地,清政府令其回國。但經南懷仁說明他們為法王所遣,精於天文曆法。次年入北京,白晉與張誠為康熙留用,隨侍宮中,其他三人回浙江。白晉為康熙講授歐幾里得幾何。1693年(康熙卅二年),康熙派遣白晉為使出使法國。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白晉、雷孝思等傳教士,奉帝命測繪中國地圖;白晉才出京門,因座馬受驚,跌落馬下,腰痛不能繼續前行,留陝西神木縣養病,後返北京休養,集各傳教士所繪分圖,匯成全中國總圖。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賜名為《皇輿全覽圖》。
作者:歐陽哲生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香港三聯書店 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