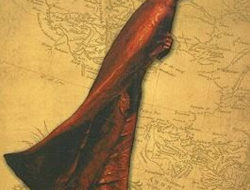编按:12月11日为狄恒神父(Reverend Father Alfred Joseph Deignan, S.J.)逝世周年纪念,狄恒神父于1953年8月获耶稣会派往香港宣教,弘扬天主教教育理念,从事各种社会服务思深见远,鞠躬尽瘁,与东方之珠结下一世之缘。。谨以此文怀缅为天主和香港奉献一生的狄恒神父。Ar dheis Dé go raibh a anam.
萌芽
嘉云(Cavan)郡位于爱尔兰靠北与北爱边境的接壤处,那里有一条名叫慕农(Mullagh)的小村庄。因为地处边关,所以常常给人利用作走私基地。特别在大战期间,由于南爱茶叶奇缺,故此,私运茶叶就成了两国边境处最频密的活动。
四十年前的某日,一位耶稣会神父应邀到村里为教友们主持避静,狄恒(Deignan)先生夫妇联同他们已懂事的孩子也参加了,当中排行第六正在唸小学的亚尔佛(Afred)则在是次弥撒中担任辅祭童。弥撒后在祭衣房里更衣的时候,神父突然转身朝小亚尔佛问道:“孩子,将来长大后有打算做什么吗?”
“我希望做神父,”孩子随便的答道。
“那么,你有想过当一名耶稣会会士吗?”
“没有,”孩子直截的回答。
回到家中,小亚尔佛走进厨房对母亲兴奋的大叫道:“妈,我将来要做个耶稣会会士。”
“什么?”他母亲绉著眉,一脸不解的望着他,“耶稣会是什么玩意?”
“哦,我,我也不知道,”孩子摸抓着后脑瓜,看来他的母亲比他更不明白耶稣会究竟是什么来哩!
原来,那位神父是第一位到慕农村去的耶稣会会士,加上一般住在农村的居民根本就不了解修会是什么,当然更遑论修会的名称了。
成长
孩子的世界是千奇百怪,多采多姿的,今天他愿望将来当医生,明天他也许希望将来当个飞机师。小亚尔佛也不例外,过了一段日子,他就说将来长大后,要做个足球明星。
事实上,到了今日,踢足球依然是亚尔佛的最大嗜好和乐趣。一九五三年,当他以耶稣会修士身份来港实习时,他加入了香港足球总会(H.K. Football Club)打右翼。据说当年与亚尔佛修士一起加入香港会的,还有现今的范育伦神父(Rev.Anthony Farren,S.J.)。
小亚尔佛小学业后,家里本已不太理想的经济环境这时更加足襟见肘。试想想,一个育有十二名子女的普通家庭,除了各人的衣食住行外,还得予以供书教学,其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所以,狄恒先生夫妇,不得不整天盘算,看看能否供小亚尔佛继续唸中学。
当家人正为小亚尔佛的前程终日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却以优异成绩考进城里一所寄宿中学,且获得奖学金而不须再为学费发愁。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他将要就读的学校竟是一所耶稣会主办的中学。自此,他逐渐明白耶稣会是一个怎样的修会团体,而他的修道圣召――特别是耶稣会的圣召――又再次萌芽滋长了。
果然,中学毕业后,亚尔佛进入了耶稣会初学院,人们开始称呼他狄恒修士。
学中文记趣
一九五三年,狄恒修士奉派来港服务。这之前,他已完成了两年初学院训练,四年大学课程(爱尔兰国立大学文学学士)以及三年哲学课程。他抵港后的第一份差事,就如当时其他来港实习的外籍耶稣会会士一般,到长洲的耶稣会沙勿略院学习中文兼广州话两年。
事隔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面对早已晋升铎品的狄恒神父,问及当日他学习中文的有关情况时,他腼觍地笑着说:“初学中文时,真是苦得很,常常都力不从心。不过到了第二年,情形就有点改变。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真够运。唔,当时长上为使我们有更多、更好的实习机会,于是派我到长洲圣心小学担任圣经科教师。”
“用广州话教?”
“对,用广州话,”他瞪大眼睛,一副信不信由你的神情,边点头边继续说:“其实除了圣心小学外,我还得在另两间中文小学任教哩。想当年呀,上课前我必定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备课。但每一次我要踏入课室时,我就心惊胆跳,精神紧张得很。”
“怕在用字方面闹笑话?”
“妳实在有所不知,我是怕学生发问呀。”
“真的吗?”老师怕学生发问而精神紧张,真是叫人半信半疑啊!
“是这样的,我虽然用中文讲课,但我却是听不懂中文的。而且,我讲课时所需要表达的说话,都是事前背诵妥的,所以嘛……。”
“哎,如果万一有学生举手发问呢?”
“就是嘛,所以待学生问过后,我就会回答他说:“我明天答你。”到了第二天,他一定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狄神父,那岂不是没有交流吗?”
“我常常在小息或下课后跟孩子们一起到球塲踢足球,就在那里,我跟孩子们学晓了许多普通的中文用字、用句。
“我喜欢跟孩子们学习,这样为我较自然和投入。”
狄神父是个很容易害羞的人,你要是跟他开玩笑,他也一样跟你笑着,然而会陡地忸怩不安起来,两颊飞红直落脖子。
晋铎
两年长洲生涯,他给调往香港华仁任教。一年后,即一九五六年,狄恒修士在港实习期满,于是奉命返回祖国爱尔兰,并在那里开始攻读神学课程,终于一九五九年晋升铎品,一九六0年获神学学士学位。
家是乐土
有一次,狄神父给我看他们兄弟姊妹十二人的全体照,有一张还是与父母合照的,偌大的一个家族,的确蔚为奇观。
“小时候,家里人口众多,父亲经营著一间小店子,还有个农场,虽然如此,家里的经济情况总是令人操心。”
“大家一起快乐吗?”
“当然快乐,我们兄弟姊妹间的感情是很好的。在那种环境中,我们学晓了彼此担待、祸福共享的道理来。”
“就像修院里的生活?”我笑问。
“是的,是的,”他不住点头的答说。
“噢,你的另一个兄弟也是神父?”我指著照片里穿着神父制服的一员,向狄恒神父问道。
“对呀,他是我四哥,是一名教区司铎,现在爱尔兰。”
“神父,有没有回故乡走走?”
“刚晋升铎品那年,曾经回去。后来就没有了,因为那一年,我进了初学院之后,家里因经济关系,把所有可以卖的都变卖掉,然后全家搬到都柏林去居住。”
青年的导师
目前,狄恒神父不单是九龙华仁书院的校监兼校长,同时也是公教婚姻辅导会的委员、香港修会学校联会主席、教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以及港府教育上诉委员会主席。
据狄恒神父自己的记述,当年他之所以加入公教婚姻辅导会(CMAC),是渴望从那里获得一些窍门,可以帮助正在情窦初开的青少年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狄恒神父说,这种现象在他的学生当中,十分普遍。看见他们因此而失魂落魄、功课骤然退步的时候,神父心里就十分难过。他指出,责骂、阻止都不是有效的途径,也不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态度。自从透过CMAC所给予的指导,狄恒神父不仅掌握了青少年辅导工作的要诀,同时且深明这项使命的重要性。
时光荏苒
生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五日的狄恒神父,于一九五九年在祖国晋铎后,即于一九六一年返回香港。这时,为要重温生疏了的中文,他像第一次来港时那样先到长洲学习中文。一九六二年,他奉命前往香港华仁书院履行新职――校务主任。
[按:当时校长为霍理义神父(Rev. J.G. Foley,S.J.),现职香港教区教育委员会主席。]一九六八年出任该校校长职至一九七0年。同年至一九七八年,为香港大学利玛窦宿舍舍监。一九七八年奉委为九龙华仁书院校监兼校长至今。
学习尊重和欣赏
狄恒神父说,他十分缅怀自己的祖国。回想当初离乡背井,抵达一个文化、种族、语言完全陌生的地方时,他就害了很浓重的思乡病。后来日子久了,本地语言、习俗都上手了,人就机灵活脱,什么样的中菜节日也能够人前人后的如数家珍了。
“在国外生活,最使我高兴的,就是学会了尊重和欣赏别人的文化以及生活习俗。能够跟中国人一起生活,我感到十分愉快。我肯定,假如我没有在香港住上这许多年的话,在我这一生中,我一定不会获得这么多!”
狄恒神父认为,要引导青少年迈向真善美的人生,音乐的薰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在校内不单成立了歌咏团,还在筹备成立一队民乐团,以培养学生们对本国的文化艺术有更紥实的基础和兴趣。
原文出自《公教报》1982.2.5
作者简介
李韡玲 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出任Cosmopolitan香港版总编辑。 九十年代与友人创办《流行通信》中文版并出任总编辑。 1998年TVB成立普通话台《八频道》,玲姐应聘成为该频道“潮流追风”节目主持人。 1994年开始在“香港经济日报”和“信报”撰写专栏。 目前,玲姐是香港经济日报、头条日报专栏作家。



![《植物情懷》, [法]馬克·讓松 夏洛特·福夫 著,戴捷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https://www.amdgchinese.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植物情懷》-法馬克·讓松-夏洛特·福夫-著,戴捷-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1-250x1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