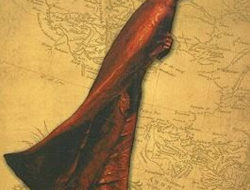几百年来,植物学家不断发现发掘世界各地的珍奇植物,同时植物也进行自己的全球化过程,我们在亚洲、欧洲、美洲等各大陆都可以见到其他大陆的树木花草。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有过怎样的历史?植物学家们有哪些传奇经历?法国科学家马克·让松在《植物情怀》中带领读者一道探查这些奥秘,让读者在阅读的喜悦中不知不觉对植物产生好奇心。

《植物情怀》, [法]马克·让松 夏洛特·福夫 著,戴捷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有关18、19世纪远赴中国为植物学做出贡献的西方传教士汤执中、谭卫道、德洛维等人的经历。
汤执中神父:在御花园上班
正是由于这位宗教人士,神父们才在中国开启了植物学之旅。当时没有任何外来者能够在这个国家随意行走,而精心挑选过的耶稣会士则能够进入皇帝的御花园住下来,皇帝本人渴望知识,喜欢与他们相处。

汤执中死于1757年(乾隆22年)6月12日,葬于北京市海淀区彰化村正福寺,他的墓碑今天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墓碑用中文和拉丁文书写。
1741年,北京近郊已经精耕细作,汤执中神父(Pierre le Chéron d’Incarville)不得已只好降低自己的期望。要想找到一些罕见的植物品种,就得走出北京。这位传教士写信给自己的植物学老师朱西厄(Bernard de Jussieu)是法国博物学家,敦促他寄来一些球茎和种子,这样他就可以接近皇帝。汤执中向朱西厄解释说,皇帝热衷花卉,为此他还专门建造了一套房子,以便欣赏到山上的春白菊,这就有了讨好他接近他的理由。
朱西厄和汤执中一共通了16封信,聊的都是有关寄送植物的事。汤执中担心商船的船舱太潮湿,于是他等待着沙漠商队经过,他们用骆驼驮著商品从欧洲各地经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随后,汤执中极具耐心地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培育了一株异域含羞草(Mimosa)。
清宫习惯称由欧洲人引入的植物称为“海西”, 汤执中向皇帝进献了含羞草,这种植物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兴趣,欣赏之余皇帝命郎世宁将其描绘下来,这就是《海西知时草图》【清】郎世宁《海西知时草图轴》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德拉维神父:跑遍云南三十年
植物探险家借此机会对中国从云南至西藏进行了勘探,安顿下来的教士们则学习当地语言,把业余时间的每一分钟都用在植物上。他们很快便成为植物学家最好的中转站,最终寄回的植物由阿德里安·弗朗谢(Adrien René Franchet)接收。在自然博物馆内,这位苛刻的植物分类学家着手接待所有由宗教人士寄回的植物,并发表相关研究,汤执中神父寄来的是第一批。朱西厄去世之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收件人,这些植物一直放在档案室中无人问津。
他们的发现规模之大,可以说是上帝的慈悲,但主要还是因为那里有特殊的植物群落,其名声大得可以越过巴黎植物园的高墙。弗朗谢收到的东西除了大包的晒干植物,还有许多种子,园丁们将这些种子种在巴黎的花坛中,每个人都想在自家花园里再现远方国度的花卉。
谭卫道神父:好运连连,遇到大熊猫,看到了山桃
这些人(编注:当时来华的神父们)的形象显然与探险家不符:消瘦、贫穷,穿着破旧的长衫,只跟穷人打交道,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势的中国人会接待他们。他们当中,只有谭卫道神父(Père Armand David)获得了一点知名度,这位巴斯克人喜欢攀登比利牛斯陡峭的山峰。
但是他们的部分发现从未在植物园以外的地方种植过,如山桃(Prunus davidiana Franch)。这是谭卫道神父在成都附近的山里发现的,那里原来是皇帝的夏宫,也正因此被园艺家们所忽视。山桃的粉色小花开得很早,不久就被冬日的寒风吹落。看到这些美丽的花儿,人们几乎忘记了传教士们在探险过程中所经受的艰难险阻。

![《植物情懷》, [法]馬克·讓松 夏洛特·福夫 著,戴捷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https://www.amdgchinese.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植物情懷》-法馬克·讓松-夏洛特·福夫-著,戴捷-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1.jpg)

![《植物情懷》, [法]馬克·讓松 夏洛特·福夫 著,戴捷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8月](https://www.amdgchinese.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植物情懷》-法馬克·讓松-夏洛特·福夫-著,戴捷-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1-250x1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