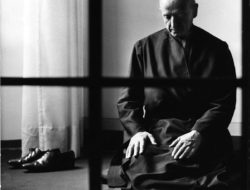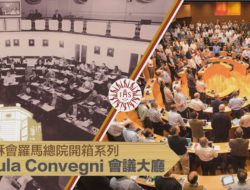余神父生于1926年,是爱尔兰人。小时候,一家六口经常一起到圣堂,每晚都会一起诵唸玫瑰经。那时他亦热衷于参与辅祭会活动,与小辅祭一起玩耍,为堂区服务,唯没有当神父的念头,甚至对圣召有些反感。中学时,他对未来尚未有明确方向,只知道要勤力读书,而且更有意投身爱尔兰曲棍球职业球员的行列哩!
18岁的时候,余神父因脚伤要卧床休息,好奇心促使他翻阅了家中一本有关圣召的书。“我觉得是天主给我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平日忙于读书、考试,没有时间去想。”余神父回想说。于是他偷看了那本书,“天主真的给了启示!祂说:‘你一定要做神父!’”而这个讯息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那时我决定要做神父,而且一定要做耶稣会的神父。”
余神父的兄长是耶稣会神父,而余爸爸一直希望余神父能够继承生意,对于他要做神父一事,非常生气。没有父亲的批准,他无法入修院,幸好在亲戚的帮忙下,余爸爸终于首肯让余神父踏进耶稣会备修院的大门。
“初期很不习惯修院的生活,多么希望院长会请我离开。”不过,慢慢地余神父适应下来,发愿后到了国立大学读书。
他在大学修读拉丁文及希腊文,一边上学一边在修院生活,这三年的时光过得很愉快。“大学生活很好,而修院里也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我参加了辩论学会又认识了皮尔斯的作品。”皮尔斯是爱尔兰的国父,他写诗、小说及短故事,更曾为爱尔兰独立发动革命,其作品对余神父有很大影响。在周末,余神父会与修生一起行山、吃?包及谈天。大学毕业后,他到了一条乡村攻读哲学课程。
不久,他被会方派往外地“实习”!在香港和非洲两个地方,他选择了香港。“家里有些关于中国的杂志,而会方在1926年起已开始派传教士到香港,我们经常都会收到他们的消息,基于对香港的认识和兴趣,我选择了香港。”
在1952年,余神父与会方一名神父和三名修士一同乘船到香港。对余神父来说,香港是一个很不同的世界,尤其在风俗习惯上,光是名字排序的分别也令他很不习惯;英文是名、姓(James Hurley),中文则是姓、名(余理谦)。
语言是另一个难题,初到香港,会方安排他们住在长洲的思维静院,并请老师教他们广东话。“广东话有九个音,学得好辛苦。”一年之后,余神父在长洲一间小学用广东话教圣经。一次,他对学生讲原祖父母的故事,“我们今日要讲亚当、亚娃(亚当、厄娃)”,这句说话惹得哄堂大笑,余神父很惘然,后来灵机一触下他索性用“原祖父母”四个字代替。
第三年,他被派到华仁书院教书,在那里他认识了李柱铭的父亲李彦和。李彦和当时在华仁教中史和中文,对中国近代史有浓厚兴趣的余神父经常向李请教。
1955年,余神父返回了爱尔兰攻读神学,并于1958年晋铎。1960年,他重返香港,到珠海书院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更担任外文系系主任。
六十年代初,香港的学生运动开始,那时也是余神父最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时期。当时一些关心社会的珠海学生在学生报上发表了有关珠海的文章,令校方很不满。被点名的12名滋事学生被开除出校,于是有学生找余神父帮忙。余神父为学生出头一事轰动全城,连当时徐诚斌主教也召见他。结果余神父写公开信表明支持学生的立场,可是12名学生最后仍是被赶出校。
“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没有被收回是失败,但为我来说是大事!”做修士的时候,余神父只能透过收音机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珠海事件对学生来说是失败的运动,但对余神父个人来说是真正亲身认识社会的机会。
在珠海事件的风波后,余神父曾先后参与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直至1972年被派到菲律宾工作,余神父才淡出了社会运动。
在学生运动期间,余神父接触到工人问题,于是在他再次返港的时候,跑到工厂工作了四个月。他在工厂负责剪衫,工作性质虽然容易,重复的工序却令神父觉得与以前的生活大有分别。
“剪衫的生活非常闷!重复的工作,it’s killing(令人难以接受)!一个教宗曾这样说‘入工厂前,一块无用的木头可以被制成椅子;相反,人到工厂时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块木头。’”
离开工厂后,余神父去避静重新思考将来的路,最后他决定从事堂区牧民工作。适逢当时一位神父邀请他到牛头角基督劳工堂工作,那里邻近工厂并以服务基层教友为主,正合他心意。“我好钟意‘劳工’两个字!而且那时我不喜欢到富有的堂区(服务),而想去一个普通(基层)的堂区(服务)。”
余神父在牛头角堂区服务了十一年,最难忘是成立了关社小组。他亦喜欢与当时的圣母军去探访教友,做家访。同时,他积极投入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关怀囚犯。其后,他先后到过黄大仙、柴湾服务。
回顾六十年的铎职生涯,以文化大革命后的一台“密室弥撒”最令他难忘。文革后不久,他有机会跟团到内地旅行。有修女知道他要到上海,就请他到家乡探望她的亲戚。
“当时神父的身份很敏感!在内地只有一间在北京的圣堂开放,让外国人望弥撒,本地人则无法参与其中。”于是神父带了?饼和酒,穿了一身便服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来到那个家庭;那是一个四人公教家庭,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小孩。
一进屋,余神父把修女的信交给他们说:“我系神父,可以帮你开弥撒。”
他们回答说:“神父请你不要开弥撒!这里会有人把这事向外人说。”原来他们害怕家里的小孩乱说话,他们只敢请神父为他们做修和圣事。余神父听了就与他们一起唸赦罪经和补赎经。
他们似乎意犹未尽,请求神父说:“神父,可以做一台简单的弥撒吗?”
余神父心想:“我要做一台妥当的弥撒!”于是他们著那小孩去看电视,然后一起进了一间房。那里没有圣经,他们奉献了饼,神父祝圣饼和酒并特别为中国教会祈祷。
“那一刻真的好感动!”他们多年没有望弥撒,感动得哭起来。
现在,余神父于圣依纳爵堂服务,继续牧民工作和关心社会,每天为社会上不同需要的人向上主默祷……
本文摘录自香港天主教教区视听中心
编按:余神父于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离港,返回家乡爱尔兰度荣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