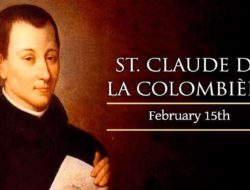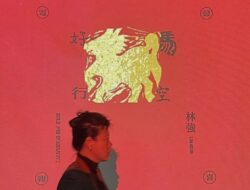甫于四月底辞世的汪德明神父,一生结出的果实累累。他入会的年代,只要远渡重洋传教,很难再回家乡省亲。但他舍下他的小船、跟随主耶稣基督,他说他打从一开始就深爱台湾,爱到忘了西班牙的家。
“没有什么事,比起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更伟大、更快乐的了。”
这是甫以94岁高龄蒙主恩召、西班牙籍的汪德明神父(Fr. Jesús Sánchez Breña, S.J.),在世时曾写过的一段话。幽默随和的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不断地结出果实,从1961年32岁晋铎后不久,便积极展开他的使命,直到87岁住进颐福园,即使困在老弱的身躯里,他仍不忘自己的使命。

2024年5月4日初夏微热的上午,汪德明神父的殡葬弥撒于彰化静山灵修中心举行。弥撒由中华省省佐墨朗神父主礼、詹德隆神父与聂世平神父襄礼,包括新竹教区荣休主教刘丹桂神父在内的11位神长共祭。
与会约百位的来宾当中,包括了汪神父曾陪伴过的台南耶稣圣心堂的学生、教友,也有早年和他一起跑遍新竹山区原住民部落、推广储蓄互助社的伙伴,还有国际溢升会的会员,以及一群穿着红领黑色背心制服的中华民国储蓄互助协会的理事们前来吊唁,并以印有会徽的蓝色会旗,覆蓋汪神父的灵柩。他们见证了汪德明神父一生,所结出的不同果实。
结出许多子粒
圣道礼仪选读了《若望福音》12:24-26:“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证道的聂世平神父同样来自西班牙,他说汪德明神父应验了这个天主的诺言,牺牲了喜欢做的事、牺牲了与家人一起的机会,重新适应新的语言、文化,为的是结出丰厚的果实。

聂神父说,汪神父怀着跟随主的渴望,经常分辨在哪里可与耶稣合作,他会观察台湾社会哪里有需要、教会在台湾应该做什么,深刻地活出耶稣所命令的“结出常存的果实”这个使命。
聂世平神父将汪神父在台湾的福传之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他投身耕耘的三座“葡萄园”:社会工作、培育平信徒、老年服务。
1960年代初,30岁出头刚晋铎不久的汪神父,留意到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义,贫穷。他连同其他神父和教友,鼓吹在社区、部落成立储蓄互助社,并推动政府立法,以聚沙成塔的力量,让一般人在经济上既自助也彼此互助,且有法律的保障。他被视为台湾储蓄互助社会运动的灵魂人物,且他这粒麦子落了地,真正结出许多子粒来,目前全台已有324个储蓄互助社,社员超过22万人。

到了1980年代,汪神父进入半百的岁数,他看见教会的另一种需要,转而投入平信徒的培育。台湾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先生在2021年接受耶稣会中华省通传中心的专访时曾说,其实早在1960年代中期梵二刚结束,汪神父便已提到,教会应该更重视教友,教友参与本来就是教会应有的精神,而不是附带的。
你叫了我,我在这里
聂世平神父表示,汪神父为了培育平信徒,写了很多和培育有关的书籍及手册。这个阶段的他,也常以《撒慕尔纪上》当中的一句经文为口号:“你叫了我,我在这里。”(撒上3:6)
但天主的仆人也会老去,1990年代末汪神父也加入银发一族,他因此注意到老人的需求。在自己迈入70之龄时,从高雄开始推动成立,针对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们,赋予人生一种新而充实的愿景的国际溢升会 (Life Ascending International)。映照台湾近年逐渐高龄化的社会,又再次印证了汪神父总是敏察时代讯号、走在时代尖端。

汪神父真的很爱台湾,聂世平神父说:“他用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他的时间,全部都给了使命。”2018年,身体已越来越羸弱的汪神父,终于获颁中华民国身分证。在领受国民身分证的典礼上他说,从一开始就爱台湾,爱到忘了西班牙的家,但是西班牙的家人认为他是台湾人,台湾人认为他是外国人,那他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呢?拿到身分证,他很感动,也很温柔地说:“我现在属于你们了,我非常高兴。”
到底,做一位传教士 (Missionary)意味什么?聂世平神父表示,汪神父给了他灵感与榜样。那不只是一个人、做了某些事,还要再加上身分,这个身分就是使命 (Mission) 。

告别礼开始前,墨朗神父代表省会长董泽龙神父致词时说:“我所认识的汪神父,十分谦逊,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充满正能量。”有位会士得知汪神父过世的消息后,写信给墨朗神父分享:“汪神父是一位很棒的神父、会士和朋友,是天主忠信的好仆人。”
告别礼结束后,随即启灵,众人在明亮的天空映照下,沿着静山夹道的绿荫,缓缓前行,陪伴结实累累的汪德明神父走完人世最后的一程。
文/图:耶稣会中华省通传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