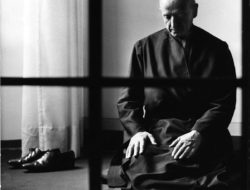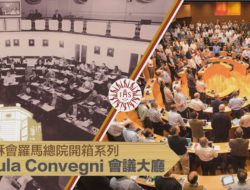早在康熙晚年,因喜爱西方珐琅工艺,马国贤、倪天爵等人就被召进宫传授。1716年马国贤在信中写道:“皇上被我们欧洲的珐琅所折服,希望其皇家作坊引入这一工艺……如今令郎世宁和我在釉面上画图,我们两人如囚徒般被日夜关在皇家作坊,周围是一群贪污腐败之徒,我们声称不懂这门艺术而拒绝他们的要求。”法国耶稣会士与意大利传教士对中方要求的态度不一样,他们采取了与清朝合作的态度,以便进一步扩大法国耶稣会士的影响,倪天爵将这项技术带入清宫,其工艺直接来自法国的利摩日(Limoges),1720年冯秉正的一封信提及此事:“事实上,御旨之下,中国的工匠制作珐琅的时间也不过五六年,然而其进步速度惊人,倪天爵神父仍然是他们的师傅。”

乾隆对欧洲工艺的喜爱不让康熙,他在位期间出入清宫的西人往往是一些具有工匠技艺的耶稣会士。1780年10月15日,方守义在一封书简中谈到进宫的三种主要才能:画家、钟表匠、机械师。此外就是翻译和天文学。乾隆对西方美术和天文学极为倾慕,在外人面前也毫不掩饰,韩国英对此印象深刻:“这位君主对欧洲人过奖了,他公开对所有人说只有欧洲人才精通天文学和绘画,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只是‘后生小辈’。您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偏爱对于一个骄傲的民族该是多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民族眼里,一切非出本土之物均是粗俗的。”
以画师身份进入清宫的传教士有郎世宁、马国贤、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诸人,王致诚在其书简中谈到他作为画师在宫中的具体工作情形:
“在皇帝的宫殿及其园林中,除了上朝之外,他很少将王公和部院大臣等权贵们领入其中。在此的所有西洋人中,只有画师和钟表匠们才准许进入所有地方,这是由于其职业而必须的。我们平时绘画的地方,便是我向您讲到的这些小宫殿之一。皇帝几乎每天都前往那里巡视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席而出,更不能走得太远,除非是那里需要绘画的东西是能搬动的原物。他们虽然将我们带到了那里,却又由太监们严密看押。我们必须步履匆匆地行走,无声无息,以脚尖着地,就如同偷着前去办坏事一般。我正是以这种办法在那里亲眼目睹和浏览了整个漂亮的御园,并且进入过所有套房。……白天,我们置身于园林之中,并在那里由皇帝供应晚餐。为了过夜,我们到达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或者是一个镇子,我们在距皇室很近的地方购置了一幢房子。当皇帝还驾京师时,我们也随驾返回。此时我们白天便留在皇宫深苑之中,晚上则返回我们的教堂。”

1754年10月17日钱德明在致德・拉・图尔(de la Tour)神父的长信中,报告了王致诚在宫中服侍乾隆的情况,包括被皇帝召到热河,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为乾隆制作《得胜图》,皇帝要封王致诚为官,遭到王致诚的婉言谢绝,以及王在宫中向大臣们介绍法国情况,并与其他传教士作画和制作报更自鸣钟、喷射水柱、玻璃器皿和自动行走的狮子等具体情形。
王致诚存世的画作数量虽少于郎世宁,但其画艺却不逊于郎氏,在当时与郎氏齐名。在入宫服务的西人工匠中,蒋友仁、韩国英较为突出,他们主持了圆明园中的欧式宫殿设计。蒋友仁在1767年11月16日致信巴比甬・道代罗什,交代他是1745年奉乾隆之命,作为数学家来到北京。两年后“应皇帝陛下之诏负责水法建设”,以为美丽的圆明园增添新的亮点:
“就是在这些花园中,皇帝要建一座欧式的宫殿,从内部到外观都装饰成欧洲风格的。他将水法建设交我领导,尽管我在这方面的低能已暴露无遗。除了水法建设,我还负责在地理、天文和物理方面的其他工作。看到皇帝陛下对这一切饶有兴致,我利用余暇为他绘制了一幅12法尺半长6法尺半高的世界地图。我还附加了一份关于地球和天体的说明,内容涉及地球和其他星球新发现的运行轨迹,彗星的轨迹(人们希望最终能够准确预测它们的回归)。”
蒋友仁曾就其在宫中与乾隆接触的情形于1773年11月、12月间连续三次致信嘉类思神父。第一封信谈及新来的李俊贤、潘廷章两人向乾隆进贡的望远镜等礼品,潘廷章为乾隆作画像,宫中的建筑风格和各种饰物。第二封信记录了蒋友仁与乾隆的谈话,内容涉及欧洲如何选择传教士来华、铜版画《得胜图》的制版、欧洲各国及东南亚、日本各地情况、当前在华传教士情况和天体运行、皇子们的学习等。

第三封信汇报与乾隆谈及天体运行、望远镜、宗教和传教士的工作,对晁俊秀的评价,葡萄酒和传教士的宗教生活等。其中在谈话开始蒋友仁向乾隆介绍了“太阳中心说”,这可能是中国人首次接触这一原理。
1774年10月23日,蒋友仁不堪工作劳累和耶稣会被解散消息的打击倒下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耶稣会士在报告他去世的噩耗时,对他在华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圆明园建造水法、喷泉和西洋楼的过程作了详细回顾,最后总结道:
“如人们有朝一日撰写中国教会年鉴,甚至只需引证非基督教徒对蒋友仁神父的说法和想法便可让后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于其才华。皇帝为他的葬礼出了一百两银子,还详细询问了他最后的病情,最终道:‘这是个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这些话是很高的赞扬,若这些话指的是一个鞑靼人或中国(汉)人,它们将使其子孙后代享有盛誉。”
韩国英在京二十年(1760-1780),据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在京耶稣会士回忆,他“关注、爱好各门学科,拥有丰富的学识;其专心尤其是其热忱使他在从事的所有工作(如天文学、机械学、语言历史研究等)中均获得了成功。”“他为北京的传教士们寄往欧洲并在国务大臣贝尔坦(Bertin)先生关心支持下出版的学术论文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从不希望这些著作署他的姓名。”

1764年11月7日韩国英致信德尔维耶(Dervillé)神父透露:“我在皇宫里工作了四年之久。在皇宫里做了一座配有喷射的水柱,鸟的鸣叫声和变幻不停的动物形象的大水钟。我经常见到皇帝。请您相信我,他只让那些违抗其旨意的人成为殉难者。如果没他公开地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会不在人世。请您为很喜欢我们的皇帝本人及其全家的归信祈祷吧。”又据其1767年11月22日书简称:“余在中国离宫御园之中,前为喷水匠与机匠凡五年,自皇帝建立武功以后,又成园艺师与花匠。”韩国英逝世后留下的遗著多收入《中国丛刊》。
注释:
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 意大利人,耶稣会士,于西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來华,为首批隸属于传信部来华的传教士。随之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擅长绘画、雕刻,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
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中国的宫廷画家将承德避暑山庄中的山光水色绘成三十六景,由马国贤根据原画刻制成铜版,印出了一套《御制避暑山庄图泳三十六景》(《热河三十六景图》)的铜版画。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的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地理史上第一部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此后,马国贤共镌刻中国地图44幅,并应康熙之邀, 将雕刻铜版技术传授给中国人。这是铜凹版印刷术最早传入中国的情况。马国贤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回国。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圣名若瑟,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画家。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皇宫任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郎世宁擅绘骏马、人物肖像、花卉走兽,风格上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受到皇帝的喜爱,也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其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瑞谷图》《花鸟图》《百子图》《聚瑞图》《仙萼长春图册》《心写治平图》(《乾隆帝后妃嫔图卷》)等。
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 法国人,耶稣会士,自幼学画于里昂,后留学罗马。工油画人物肖像。
西元1738年(乾隆三年)来华,献《三王来朝耶稣图》,乾隆时受召供奉内廷。初绘西画,然不为清帝所欣赏,后学中国绘画技法,参酌中西画法,别立中西折中之新体,曲尽帝意,乃得重视。与郎世宁、艾启蒙、安德义合称四洋画家,形成新体画风。
艾启蒙(Ignatius Sichelbart,1708—1780),字醒庵,生于波西米亚(今属捷克),耶稣会士,1745年(乾隆十年)来中国,师从郎世宁学画,得郎氏指授,使西法中用,很快受到清廷重视,诏入内廷供奉。
他擅长人物、走兽、翎毛类绘画,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被人称为四洋画家,形成新体画风。他已知的作品有紫光阁武功图中《准噶尔战功图》(1755年,乾隆廿年);孝圣皇后八旬万寿(1771年,乾隆卅六年),《香山九老图》,着录于《国朝院画录》;《十骏图》(1772年,乾隆卅七年)。《宝吉骝图》轴(1773年,乾隆卅八年),绢本,设色,藏于台北故宫。
贺清泰(Giuseppe Panzi, 1734-1812),原名Louis Poirot,法国人,耶稣会士,曾经留学意大利,精通天文学、数学,于公元1770年(乾隆卅五年)来华,不久便进入宫廷供职。
潘廷章擅长作油画肖像,曾为乾隆皇帝绘制油画肖像。他在公元1773年(乾隆卅八年)画的《达尼厄乐先知拜神图》受到蒋友仁的推崇,认为精妙不在郎世宁之下。存世作品极少,现所见到的仅有半幅,即故宫博物院藏《廓尔喀贡马象图》卷,是其与贺清泰两人合绘,后面所绘两匹马,是现知潘廷章的唯一真迹。
贺清泰与《古新圣经残稿》文言文之外,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也常以白话文著译,而其集大成者,非属乾嘉年间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中译的《古新圣经》残稿不可。《古新圣经》之所以为“残稿”,因贺清泰并未如数译毕武加大本《圣经》(The Vulgate Bible)七十二卷。生前,他仅译得卅七卷,但已达一百万余言。虽然如此,贺清泰仍为所译写了两篇序言,而且是北京土语与北京官话混而用之,书序史上罕见。第二篇序言中,贺氏引述了圣热落尼莫(St. Hieronymus or St. Jerome, c. 347-420)因好西赛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前106-前43)华美的文体(style)而在梦中为天主座下的天神鞭苔的历史名典,将之附会到《圣经》中译去,坚信唯有用乾嘉时代的北京俗语译经,方能显现天主托人写经的本意。因此《古新圣经》用北京俗语中译,可谓天主教“有意”用白话书写最明显的例子,也是《圣经》首度以中国通俗之语翻译的首例,可视为清末以前最重要的白话文书写成果,而且还是胡适所谓“有意”为之的白话文书写成果。
蒋友仁(P. Benoist Michel),字德翊,原名伯努瓦·米歇尔,1715年10月8日出生于法国欧坦,于1774年10月23日逝世,法国耶稣会士、法国传教士,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家。
公元1743年(乾隆九年)抵澳门,经钦天监监正戴进贤推荐奉召进京。入京后,埋头学习满、汉语言文化、孔孟经典、哲学、历史等中国传统文化,1747年才委令他办事。他不仅精于建筑设计,而且又熟谙铸造技术。曾参与圆明园的若干建筑物的设计。他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增加新疆、西藏测绘新资料,编制成一部新图集《乾隆十三排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最终完成了我国实测地图的编制。著有《坤舆全图》、《新制浑天仪》等书。他还曾译过《书经》、《孟子》,译拉丁文《书经》十分审慎,其了解汉文之深,与译笔之忠实,远出以前各译本之上。
韩国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 法国人,耶稣会士,其所翻译的《孝经》全文法译本 “Hiao-King, ou Livre Canonique sur la Piété filiale”(1779) 是目前确认的近代欧洲早期五种《孝经》译本之一。
此译本收在其名下之《中国古今孝道》(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一书中出版。
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法国人,耶稣会士,1750年抵华,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的许多作品让西方世界更加了解了远东地区的思想与生活。
他撰写的一本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出版于巴黎,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其他著作主要记录在《中国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共15卷),其第12卷〈孔子传〉(Vie de Confucius)比在华传教士先辈们整理得更准确、完整。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年-1730年) 法国人,耶稣会士,一作白进,字明远。1678年加入耶稣会,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选派出使中国传教,出发前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入法国科学院为院士。同行者有:洪若翰、刘应、塔夏尔、李明和张诚。
1685年3月3日,使团自布雷斯特起航,途经暹罗时,塔夏尔被暹罗国王留用。其余五人于1687年(康熙廿六年)抵达浙江宁波。因海禁未开,洋人不能深入内地,清政府令其回国。但经南怀仁说明他们为法王所遣,精于天文历法。次年入北京,白晋与张诚为康熙留用,随侍宫中,其他三人回浙江。白晋为康熙讲授欧几里得几何。1693年(康熙卅二年),康熙派遣白晋为使出使法国。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白晋、雷孝思等传教士,奉帝命测绘中国地图;白晋才出京门,因座马受惊,跌落马下,腰痛不能继续前行,留陕西神木县养病,后返北京休养,集各传教士所绘分图,汇成全中国总图。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赐名为《皇舆全览图》。
作者:欧阳哲生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香港三联书店 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