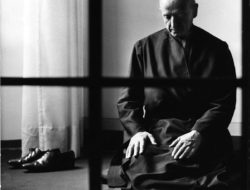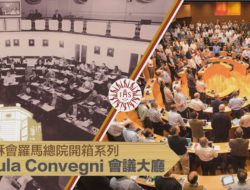问:请问神父来到中国的经过。
答:我来中国已经41年,我是1969年入耶稣会,当时开始读神学,我跟长上说我 希望能够到国外去,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好。之后长上果真 如我所愿,派我到很远的地方-中国。于是就先派我到台湾去学习普通话,那时 候说“国语”。其实那个时候在法国就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对中国有兴趣,也有 一点研究,加上当时对中国的气氛很不错,就这个样子开始的。然后我在台湾新 竹,那时有一个华语学校,在那边读两年的普通话,然后我去辅大法学院,那时 叫法管学院,我在那边帮忙一年,之后我到神学院读三年的神学,1975年毕业之 后,长上派我到国外继续读书,所谓的国外就是法国,在巴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 院(EHESS)读社会学,还有神学,那个时候南耀宁也在那边。
之后我在武汉大学,找到一个工作,是法国政府在那边办的一个交流活动, 教学方面的工作,在那边三年。第三年的时候,我去香港时,都会找马远程神父。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孙神父),就这样组织在一起,想想中国的问题。我 们那时候有四个人,南耀宁他正在写论文,马远程在香港有工作,还有另外一个 孙神父,也是刚读完两年书,好像是这样,我不是那么清楚,那我还有在武汉大 学一年。那我们三个人(+马、南)在法国,聚在一起说,能不能做些什么,那 个时候劳神父正准备退休,所以谁做这个决定我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有人问我 们能不能继续CNA这个工作,我们以后换了名字,不过差不多。那我们说,既然 长上要我们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可能要做吧。不过,劳达一好像是1982年退 休,我们只能够1984年开始,所以有一年的时间(准备)。我是1983年9月份, 到香港去做这份工作。(我到的时候)马神父已经在那边,孙神父也在,然后我 们就在那边开始准备工作,南神父大约是1984年3月份左右,才能够到香港去工 作。 那个时候我们的计画是这样子,我们叫“维信”,取郑维信的名字,那为什 么维信,因为我们说,一方面希望大陆的人在内地能开放,也是希望能够帮助耶 稣会了解中国的情况。
1983、84年,已经有改革开放政策出现,那开始的时候, 马神父就是继续在中文大学教书,孙神父他在CNA,南神父他是负责推广,需要 主持一些研讨会、会议这一类的东西。所以1983年9月开始准备工作,计画从1984 年1月开始发表CNA,大概就是这样。我从1983-1986待在那边,然后1986年需要 2 派人再到中国去,这个是等下我会告诉你,1986年,长上问我能不能到内地去工 作,我觉得也行。我就经过朋友的邀请等等,有点偶然的,我在北京找到一个法 文编辑的工作,当然那时候我就离开CNA,但是常常跟他们一起,买书啊,偶然 一点,会帮忙写一点文章,不过我记得不多。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好像是1期。 因为我虽然到香港去,但是一年就去两次,都是买书,买一些不同的书籍、作品。 这个是到1986年,大概到1991年。1991年,我去四川在一个公司工作几个月,然 后最后一年,就是1992、1993年我回到北京去,那时候是一个朋友请我去帮忙工 作,也是一样做外文编辑。 1992年,长上说,那时候是张春申神父,准备要CNA、维信搬到台湾去,这 个过程我不是这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他们就这样决定。那时候就准备成立社会文化中心,由刘家正神父作主任,我来帮忙,所以大概是1993年8月份 左右,我就到中心去,一直到2004年,总共11年。
1995年搬过来台湾,当然是因 为1997年的问题,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看报纸,作clippings,剪报,主要就 是这个,好像也写了几篇。 CNA那个时候名称改变,本来是“中国新闻分析”,后来变成“中国消息分 析”这一类的。因为在台湾登记的时候需要换名字,不过内容是一样的,外文还 是一样China News Analysis。所以看报纸,一直看到1998年CNA停刊,大概是啊, 这个事我不太清楚。我知道那个时候,M. Broseau孙神父已经离开了,没有到台 湾去。马神父哪一年走的我不记得,大约是1998年,我是一直到那边收起来。那 停刊之后,我还是负责中心,那时候关秉寅当那个主任,我知道我做三年的主任, 2000-2003,最后一年,我同时作翻译研究所所长、负责人,作两年。我们那个 时候,还是跟大陆,保持一些联系,都是比较学术方面的,特别是社会工作。 像有一位助理,叫林桂碧,她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另外一个助理,他是在辅 大图书馆,不过这个跟CNA就没有什么关系。CNA停刊后,我们就已经开始不订报 纸了,社文中心后来转型,CNA可能就是已经完成了工作,因为情况不同了。有 更多了人可以研究中国,没有那个大的必要、明显的需要。2004年,我就转到澳 门利氏这来。那当然这跟CNA就没什么关系。不过,现在还是常常,研究中国的 议题。
问:所以,神父2004年以后一样是在做中国研究嘛?
答:说研究恐怕太大了,不过关心的对象还是中国,特别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因为本来我的研究范围就是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变迁,那我还是很感兴趣。现在 所作的不能说“研究”,比较像是继续关心,继续看别人写的书,或是新来的资 料。我写的文章不多,书评比较多,文章大概一年就是写1、2篇而已,不算多少, 多半是有关社会变迁的议题。比如最近,为法国的刊物写了一篇大概介绍中国情 况的文章,另外一篇是关于社会工作的新发展,大概就是这样,现在正在准备一 篇简单的东西,社会凝聚力这类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问:神父待过香港、台湾、大陆内地,现在在澳门,在两岸四地作研究,或是关心中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研究心得?
答:对,两岸四地都跑过了。喔,当然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说,我开始的时候 在台湾,我没有准备到大陆去,因为1970年代,去大陆不太可能。台湾经济刚刚 起飞了,所以台湾有不少的工作,结果说长上要怎么决定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大陆了解的非常少,因为一方面就是因为在台湾不是那么方 便,那时我在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还在,所以你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是集中在台 湾的需要,还且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 然后我去大陆那,当然是完全不同,那次是1980-1983年在武汉,刚刚开放的, 不过开放的不是那么明显得,现在当然比以前好多了。
比如,我们第一次去,我 们的签证,光是为了武汉市,我们要离开武汉市,我们需要一个旅行证,所以, 以后当然越来越开放,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了解中国社会,对这个中国政府的 兴趣一般,不过,我去大陆之前,在法国已经产生有关中国新发展的兴趣,所以 稍微眼光转到台湾、大陆去。不过,同时也可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不要把台湾 淘汰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读书没有准备去大陆工作,然后当然, 我去大陆之后,态度就有一些不一样,不过真正了解中国各方面的互动发展、社 会变迁,就是在香港,1983-1986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天天要看报纸。
记得那个时候,你知道劳达一的工作就是听广播,那我参与CNA工作的时候, 我们还是收听湖北省的广播,其他省分就没有,为什么是湖北我记不太清楚,可 能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湖北日报。六个月以后,那时候有一个“裴先生”, 裴是什么裴我不记得了,是在帮忙(听广播)的。他是跟劳达一工作的一位老先生, 本来他是辽宁人,东北人,裴先生听广播后写下重要的消息,然后我再看看。这 些纪录应该还在我们的档案里面。不过好像是六个月以后就不再听了,不需要了,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订得报纸很多,越来越多,增加不少困难,要看的东西很多, 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掌握的。有多少报纸,现在我不清楚,可是越来越多。后 来搬到台湾来,东西(档案资料)实在是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光是看 报纸,就够忙的了。 有一些人,会先过滤报纸、先选一些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再看,决定哪些文 章重要。所以学习看的很快,这个是要技巧的。
本来我的论文,也是这方面的工 作,从报导,来挖出一些讯息。可是没有多少人用这个方法。因为需要花很多的 时间,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很特殊的方法,来了解、作比较的。当然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我看多少份报纸,我们可能一个人一天有看十份报纸以上。几乎我们每 一个省份的报纸,都有。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报纸,不过很多。所以作比较,看看 情况,看看他登的照片,这个是我比较有兴趣的,南神父他是比较中央政府方面 的,感兴趣。马神父在学术方面的思考,他们的兴趣也在这里。所以大概我们有 这样不同的分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在香港,1983、84年开始做“维信”,我们还有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多少,这个主要是南神父和马神父,作的不少。我们办了,我不记得几次,但是至少我在香港的时候,至少办两次的讲习会,不是座谈会,比较 大的甚至持续2、3天,为了耶稣会的。 那第一,因为马神父认识很多人,所以有很多相当不错,很棒的人来给我们 介绍中国的情况。参加的人第一次,不知道可能南神父跟你讲过了,就是我们耶 稣会的负责人,然后就是在不同国家里面作刊物、出版工作的主办人。我记得第 三次以后,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了。所以,有研究没错,但是我们希望这些研 究能够有很具体的帮助。
我们这个作了多少,这我不敢说,不过,是继续作的、一直作的。虽然我在 香港三年而已,但是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跟劳达一作一样的 工作,这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我们没有他那么聪明,另外一方面,开始有别的 机构,开始做这个工作。同时,因为大陆开放,所以,劳达一的看法或是这种传 统的作法,可能不是那个那么,不能说需要,但是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以前就是有他,还有几位人,China-watcher,就是这个工作,然后就更多。 比方说在中文大学就有一个中心,中国服务中心、关信基啊,我们都认识, 他是跟我们真的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在很多比较研究性的方面,他都会帮忙 我们。我记得我写论文,大概是1977年,还是1979年,我不记得了。那我去香港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旁边有一个中心,就是很多美国学生,或是其他各国 来的人,不过都是秘密的,很难很难有记录的。但是那边的资料,多得很。所以, 一些分析新闻,当然有不完全一样的作法。而且,譬如在北京的美国使馆,那时 候他们有很多人,就是在四川、湖北什么等等的。 那我们的特点,可能是比较整合性的看法,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是研究某一 个地方的,但是我们希望能作一个整体的,整体的看法。然后我去香港,很明显 的,要做的工作就是继续发扬CNA。然后我回到大陆去,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工作, 就是纯粹只做编辑等等。我了解中国的社会,可能了解的比较多,直接的,但是 几乎没做任何研究,作的有限。回到台湾去,那这个继续研究没错,可是,我没 有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史这些的,南神父他做过这个工作,可是我没有。所以 就推动一些交流,和上海复旦大学,政治文化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等 这些的。
问:这些交流是跟其他学校法语系的交流吗?
答:不是,那个时候,在人民大学,我不记得是为什么,那时,我们跟辅大的社 工系,一起与跟他们联系,最后就是,跟复旦大学的法律研究所,有一些交流。 这是我负责的,跟他们做这样的交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跟每个地方的角 度都不一样。等于说,开始我到台湾的学校,然后在香港,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新闻的分析、写文章,几乎我们那个时候每个月都要写一篇分析,那要看很多的 资料。然后,在大陆工作,几乎没什么研究。在台湾,我写的少,但是看的资料 多,然后推动这个交流对台湾很重要的。但现在在澳门不同了,现在是做真正的 5 研究不多,但是其实有兴趣看看社会变迁发展,然后去帮忙澳门利氏了解,看看 社会变化的一些现象。就是,都是帮助别人,适应社会新的环境。大概就是这个 样子。
问:那为什么耶稣会本身,像是CNA(China News Analysis,中国新闻分析,以下简称CNA)之外,还有利氏学社,对中国这么有兴趣?
答:那我很难替别人说话。我们一般来讲,对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感兴趣,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的。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信仰来看,就是说历史的过程,我们相信,一个人在历史中,可以去满足自己的渴望,就是跟天主结合。所以呢,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有兴趣。不管是在非洲、美洲,还是太平洋的小岛啊,什么的,都很感兴趣。当然,对中国,肯定是,感兴趣的,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等等,这边文化这么丰富啊,当然会有兴趣。
不过,我总是说,我对中国有兴趣,不过并不等于我对其他地方就不感兴趣。因为人有限,所以我不可能关心所有的人,所以我集中摆在一边。所以,我不敢说,我不会说什么大的理论,说中国文化是全世界重要的。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对我来讲,哪边有人,所以我们去哪边看看。我常常说,他们可能对我,不是可能,是肯定,对我和我的信仰没兴趣,“狄明德是谁啊?那个天主教的?”可是我有兴趣,看看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跟我不一样呢?
所以,如果他不欢迎我,没关系,我说“我对你们有兴趣,我不是说来教你们什么的”,当然希望分享我自己的生活观,甚至于我的信仰,不过,我在大陆能够真正讲我的信仰的机会极少,虽然现在机会多了,但是现在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没关系,我去看看可以啊,你跟我不同,好那跟你交谈,看看。所以这个是我本人的,我相信,有人会说,中国文化什么的,我不否认,可是这不是我的最明显的思考方向。意思是说,很简单的,中国文化,过去历史中很多丰富的文化,这些等等,就我了解的,现在的情况,(中国文化)留下来的,不多,也可以说不够。所以,有兴趣看,可是不是我研究的方向。意思是说,我不是一个汉学家这一类的,可是我说,现在的人,当然,现在的人不能说他们没有过去,所以你不了解他们的过去,很难看清他们现在的情况。
不过,我们有神父,他们有真的是研究中国文化,我不是。马神父比较了解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去拜访他,我不记得是为什么,可能是要给他某个神父的论文,我去他家,那时候他年纪很大,那讲什么我不记得的。所以有人研究梁漱瞑啊,或是这类的。有的时候,我对一些哲学家,或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理论,有一些疑问,比方说有一些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不是主流派的,说什么人有这个理智,我感兴趣看看。不过,可以说是不是真的作研究。第一,中文方面,对我来讲,有一点太古了,所以不容易懂。所以,为什么耶稣会有兴趣,可以说是我们的传统,哪里有人,哪里有兴趣、了解人。我们说天主好了,天主的关系,都是离不开历史、离不开现在的人。所以,这个是我的解释,所以,特别是说在CNA那边,我们讲的文学方面、历史、文化方面,不是那么多,我写的文章没有,都是当代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耶稣会的一个传统。不知道其他神父你访问的到底怎么样解释的?
对,我了解,也赞成南神父说的,从15、16世纪天主教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就变成天主教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我不会说,中国比谁更重要。所有人都是同样的重要,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当然,中国人多,更多的人,例如说,如果我们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对我们的信仰,实在是毫无关系的,那我们会说,那我们相信什么,是不可能的。可是不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要强迫别人接受我的信仰,不是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的。或是,的确有,中国在我们教会,尤其是耶稣会里面,有这个传统,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利玛窦啊等等,可是对我来讲,那个不是主要的一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可说,在法国的耶稣会,对中国确实有兴趣,也有传统,在那边去工作。比如,我们比较少到南美洲,非洲一些地方的,印度有啊,可是以后就没有了,不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印度是不可能的。好吧,那就去中国好了,因为那边有人。所以在法国耶稣会的传统,走向中国是很明显的。所以,很自然的。比如呢,日本好了,或是韩国的,不多,印尼不多,越南多,因为历史关系,马来西亚没有。当然你要说马来西亚和中国比较的话,那这个比较的话,不过,有些很自然的因素,因为大家都谈论中国的,所以感觉上中国没有这么遥远,人从这边来、这边去啊等等。那西班牙人去南美洲、中美洲也比较多,来中国的相对也少。对我来讲,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想法是中国是亚洲社会的,旧世界的一个文化,没有。
不过,的确我发现,从台湾来说,从第一次我去台湾,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台湾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可是以后我发现,好像我能够适应喔,也有兴趣,所以,如果他们派我到非洲,还是什么地方去,会不会同样的适应,我不知道。不过,我发现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六年,我不后悔,不后悔。不过可能别人后悔把我带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会说,这个国家是旧世界的一个文化等等,没有这个问题。我知道在其他地方,有人会特别研究国家啊,或是这个其
他宗教,好啦,不否认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宗教、教堂,不是我的范围,所以,这个,这个不是说不重要,很重要,可是不是我的范围,这个文化比较也不是我的范围,我就是说,那边有人,他们怎么活着呢?他们有什么?很简单的这种了解。
可以这样说的,比如我回到北京去1986年,那我为什么去呢?那边也不能研究,也不能做什么,可是我说,我想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所以我发现,不过我这个理论,没有什么太多的提出,他们,就先说他们好了,你每一次要讲说要抓住文化的差别,可是你最后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别,
可是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你说这个某某情形是文化的原因,可是同样的情形可能在国外也有,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那这个可能是社会学或人类学会关心的范畴,不能说是偏见。你要抓住差别,可是同样找不到差别,但是最后还是有。好比灯光,你要抓它抓不到,可是它的确是存在。我常常会说,这个现象在这个中国发生的现象,我们很可能在其他文化的地方,可能是历史过去或什么的,也有。
譬如有一次我写一篇简单的东西,关于社会问题,有人说西方国家强调个人的价值,东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价值规范。对是对的,但是太简单。中国在个
人主义方面也是蛮强,可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你说是以家庭为主,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家庭、三代同堂的情形,没有了,不是没有了,在农村里面还有,可是越来越少,在城市里更是不可能的。或是讲过年好了,我去台湾的第一个农历年,有一次我去新竹有一个学生邀请我去他家过年,非常传统的,在新竹市。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不同的现象产生,他们吃完年夜饭就要各自回家了,本来传统应该是要全家子一起跨年到午夜十二点,现在呢你去哪里过年?你去泰国或什么其他地方的,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也就是放假一起去旅行,可是如果全家一起跨年、吃团圆饭呢?我常常跟学生举这个例子,所谓的团年饭本来应该是出席、大家在一起吃,现在变成不一定了。这个过年左右的时候,可以聚在一起好像就差不多了。那在大陆也是一样,我在北京有很多同事,他们是上海人,他们过年不会回去的,“回去麻烦得很,等有机会再回去!”不需要了。
举一个例子。我还记得我在法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家庭,如果家庭环境许可,三代同堂是肯定的,可是现在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不否认家庭的价值,可是是否
真正是属于中国文化呢?这种想法不属于主流,但是是存在的,有一些中国人是这样说的,当前注重的是个人价值,家庭比较不重要的,我这样讲太简单了,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论述。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事情、观点,来了解,倒底我们哪里不同,但的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每一次,我们都只能抓一部分来了解,所以要把你自己的想法稍微向外扩展一点,看看是否能更加认识“人”的基本不同。我觉得台湾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家庭观等等。我现在特别注意的,因为以前我们去农村的机会太少,那我现在就是认识一些来自农村的朋友,农村还是所谓比较传统的,可是这个传统的定义可能还要考虑一下。那城市的人有另外一种想法,比如说你传统的话,那你18岁就要订亲之类的,20岁左右爸爸妈妈就会催婚啊,担心你找不到对象啊等等,你到城市里面去,没有人要结,“我没那么多钱,我现在好好工作,”那会不会有别的后果,或是其他男女之间关系的新现象,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好啊,这就是不一样了,18岁结婚、20岁订婚,如果你在农村里面,这一切都是可能的。那是否社会学能够决定一切?社会发展的方式?那这个我不觉得的,我会说社会学帮助我,开出一些不足够的理由,这个是不足够的解释,这些理由,那这个是对的,但是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事情。所以,社会学不是来决定,不会代替哲学,可是帮忙做一些解释还是有可能的。
有一些社会学的学派特别强调这一点。有的不太喜欢,特别是我刚说的这些例子,这个中国的变化,很明显会被扣上“传统”的帽子,不一定。那个时候是
在台湾,19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慢慢离开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有很多的现象出现,家庭问题什么的,有人问这个家庭价值是否能从文化里面成为一种既得价值?可是我们开始有一些,不是怀疑,可是不同的看法。现在的确是有价值,还是有价值,可是生活方式不一样了。那个如果祖父祖母很长寿,跟孙子住在一起,比较困难。因为父母说“对不起,我孩子这个教育方式是我要来决定的。”那祖父母可以帮助孙子,可是决定权在父母。所以这个比较明显的。那同时,另外一个是老人问题,我们要和老人一起住,因为要照顾父母,可是往往照顾不来,所以,安养院这么不好嘛?要看,可能这个老人家自己也比较喜欢孩子每个礼拜、每天去看看他们,老人家可以在那边不用担心、操心,有自己的空间、交友,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慢慢地同时在中国、欧洲发生的。
以前,把祖父祖母送到安老院,不过现在安老院是蛮好的,在医疗设备方面也比较安全等等。我不是说这个状况是最理想的,不过在中国现在也走向这个方
向,台弯很明显的。所以,也慢慢在接受。也有老人家觉得这样很好,“我可以在一个小地方,然后我的孩子假日来找我,或者我去找他们”等等这一类的。这样看来反而是另外一种好事。随着时代变迁,生活也有所改变。对我来讲,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现象。所以你看,研究的程度,可能恐怕不太够。那为什么是中国,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因为我想到远一点的国外去,就这样。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哥哥也是在非洲工作,就说好吧,那这样我去中国。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派我到马达加斯加。
问:那神父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当时?
答:当时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可以这样说的,因为我知道的很少,我去台 湾的第一天我不会讲中文,英文,也不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台北的飞机场, 早上10点钟,那时候还没有桃园机场。那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接我。那怎么 办?好热,那可能法国南部也是一样热。后来我在机场遇到另一个外国人,问我 在干嘛,我说等人,所以我没有说,中国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没有说我很好 奇。那我去别的国家,当然是我要适应。第一,就是要学语言,那本来我不是那 么好的学生,不过那个时候,的确是蛮用功的,因为我怕那个,因为如果我们(语 言训练)两年以后还不会中文,就可能会被赶回去。而且一个很明显的是说,你 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当然要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怎么说话你怎么说话,你 先适应,然后如果有一些想法,就在考虑。可以说是很自然的。当然,开始的时 候有一些,不太容易了解的事情。
给你讲一个例子,这个我常给学生说,第一,假如有人请我吃饭好了,不是 有碗嘛?那我们在法国有一个礼貌,就是留在盘子里面的东西你必须吃,你喜不 喜欢都要吃光,但是在这边,吃饭时大家都拼命夹菜给我,一直说“来来来”, 到最后,我只好跟他们说,对不起我实在是吃不下,所以有人跟我说,“你不一 定要吃嘛”,你留在那边一点东西我们就知道你吃饱就好了嘛。那就这样我知道,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需要了解就可以了。 不过,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在中国,如果你感觉到不好意思时候, 你露出腼腆的微笑,法国人就绝对不是这样,如果你不好意思,那就会脸长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比较了解。我跟你讲很严肃的事情,你跟我微笑,好像你在笑我,其实不是的,你的微笑是表示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会微笑。总 之,这都是需要时间了解的。
或是,(在这边)长上问你一个问题,那并无不一定代表他要你回答,你不同意的,你不一定要在他面前说,“对不起,我不赞成”。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表达。这是我自己发生的一次经验,我以为,既然你要我说,那我就说吧。可 是其实,并不一定要那个直接的对他说,你有另外一个方式表达。所以这些是很 具体的例子。 比如我现在在广州区,里面有很多非洲人,我们会有教会上的往来。而他们 表达的方式,和中国人很不同,跟我也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彼此了解、接受,那 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彼此知道。无论怎么样,我还是法 国人,虽然我在中国时间很长没错,我在中国的时间比我在法国的时间还要长, 但是,因为我教育的背景不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改不过来,也不是改不过来, 应该说是很难改,也不需要改,所以我还是保留我的反应。所以我发现,孩子时 期的教育,影响真的很深。你无法改变很多在那个时候建立的观念、习惯,也没 必要调整。这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只是一些简单的分享。
问:神父认为CNA的价值在哪里?
答:那个时候,有两个价值的,劳达一的价值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跟你说过Mateos神父,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西班牙的刊物,也是用劳达一的资料,来写,不
过这个后来作多久我不记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让CNA的工作有一点意义了。那CNA的价值,劳达一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作的工作的价值,可能没有劳达一的那么明显,因为已经开始有不一样情形,我知道关信基他说CNA不是firstclass,但是它仍然有一定重要性。它每两个礼拜、每一个月就可以出刊,本来
是一礼拜一次,后来两礼拜一次,之后又改成半月刊。这样两个礼拜一次的报告,可以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对很多人有这个帮助,他们可以很快,关于某一个题目,可以获得一个整合性的报告。那我知道很多在香港的公司企业,他们要这些报告,了解情况。一样,在相当多的使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人看那么多报纸,写一个综合性的报告,所以他们喜欢我们的东西。可能,学术方面的,这个工作不如China Quarterly这一类的,不过我们是当时的 China
Qarterly。
比如我做的工作时,1983-1986年,我们说我们不会超过的,基本上两个礼拜的消息,最多是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的资料,那我说这是背景,但是不是
那个星期的。我们往往就是两个礼拜内,所以这个就是有价值,了解情况,第一。那第二,至少我那时候的情况,避免用人民日报,你说人民日报大家都可以看,那何必来给别人重复的、他们可以自己看的东西?那像劳达一他根本不用,所以我们用的消息,就是地方性的。至少我在CNA的时候是如此。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publisher大概是Brosseau博士,chief(editor)那个时候是我,没做什么,不过我们的确是每两个礼拜要写一篇东西的。那我们说,这几天,这两个礼拜,这一个月以来,不超过一个月,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的价值。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记者,所以我们不会注意特殊事件,也不会随风起舞,我们写的方式不是记者,我们是半学术性,半新闻性的,因为如果你要
写新闻的话,报纸报纸、日报这一类的,你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来下笔,可是我们这一方面不是我们的训练,第二方面,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要写的“报告”,可以说我们写的是一种报告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特别注意这一点,在这一方面,一直到那一年,我刚说的,有它的价值。对啊,你看,我们是1994年左右在台湾嘛,1998年解散,4年而已,那时候我们越来越发现,可能,虽然我们觉得还有一些价值,不过别人可能,我看Newsweek或其他什么报纸就够了。不需要这个分析报导,尤其它是英文写的,所以在台湾连中文的报导都不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好吧,就不需要了。可以,我可以说,在香港的时候还有它的价值;在台湾,我们写的报告,我觉得开始的时候还有,还有一点,但是呢,慢慢没那么明显的价值,而且我们人也没了,所以就这样。作这个压力也蛮大的。我不是说,我们搬到台湾去是不对的决定,有别的因素在里面的,但是可以说,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的事情,我觉得还有它的价值。可能你看一、两期,对中国有点概念,但是如果你长期看一两年,那么对于中国可能就知道的不少。这些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身边很多的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选举,我那个时候写得,所以我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在看看不同的地方,他们选举的方式啊等等,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表,1这样我们大概就
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就不需要查上海、湖北的资料,因为我们都已经有这些东西。或者有一次我们介绍某一个机构的主任,他的背景,那这个对很多人是很方便的;可是现在的确,有别国的一些刊物,也有作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就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也是说,我相信现在更明显的,你查google或是什么的,你可以知道的很多,所以价值大概是新闻,还有我们的分析。可是我们分析的,有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避免有黑白的判断,很明显政府的一些作法就是不符合我们的口味,但是我们不会很明显去攻击,这个倒没有。劳达一就很明显,他的立场,不过,很可靠,他的想法的确是比较反共一点,不过他每一次说什么东西,的确是有根据的。我们可能没有他那么敏锐,可能没有。如果你看,我记得,劳达一写他的文章的时候不能说是每一期有一个中心主题,有时候有几个主题的,那这些都是小段小段;那我们那个时候,我开始就不一样了,每一期有一个主题,所以在这之后,每一期才有主题、名字,这个是劳神父以后的事。我知道一个Feature,第一个是我写的,可是小小的,我们介绍一本人民日报介绍的法国书,内容是说历史不是科学的,那这个是假想的问题,社会这个就发展了。2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不过我在负责的时侯,我们文章论述的方式,跟劳达一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有人,不是直接跟我说的,我后来辗转听到,“喔以前,参考资料非常的多,你们是很少,几乎没有,”我们的reference如果你看,其实很多,不过可能有的地方是有错的,这个错通常是页码的错误,不过人一般来讲,不会查这些东西。不过的确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错误,不多,不过有,不过基本上你看,
我们就是每一次,参考特别多东西,而且你会注意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报纸为主,至少我在作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要看中国各个不同的点,那这个是劳达一的传统,他用这个广播,我们用地方报纸,不过,方向是一样的。中央说什么,当然都可以写没问题,但是要看看地方又是怎么叙述这些事情的,当然,因为这些报纸都是正式的,或是政府出版、党出版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如果你细一点看,看这个、看那个,那就一些不一样。所谓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群众、或是老百姓的反应,要怎么解释。
对我来讲,政策用什么方式,来介绍给一般人,是他们的沟通,所以,往往在那边,我们会发现另外一方面。某一个政策好了,我们会问,这个政策有什么好,有什么特别的,那他们解释的时候,会用这个方法说,他们面对的是“这个问题”,那就有意思了,因为如果他们面对这个问题,表示这个现象就已经存在,那我们注意这一点。我现在想不出,什么很明显的例子。有一次我们作好像是精神污染,3那个时候候邓小平说,我们要避免文化污染这一类的,那个时候我知道劳达一喜欢这篇,那个时候我们说什么,其实邓小平讲的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可是到底他说什么?可能他说我们现在要小心,我们会失去人的,不能说信任,就是人的依靠,才会走到你自己的路,他们的想法,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他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是反对科学,也不反对什么,他们自己说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那最后怎么样,你到底为什么,你说什么,你不是反对西方的什么什么,而是说,年轻人他们是否,越来越脱离我们,所以这是从另外一面去了解。所以看这些文章,有那么多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那我们说,到底是什么?去看看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主要我们分析,你们说什么。可以这样说的,我们反对你们说什么,但我们听你们说话,然后你说这个也说那个,我们就搞不清楚,或是按照我
们那时候说的,好像就是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所以,可以说批判性不大,但是因为我们倾听你们说什么,所以我们有一些问题,那你怎么回答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分析“他们说的话”,这个是可能,在当时CNA的价值。那像如果是China Quarterly或是这一类的,那你不可能作一个研究,比如说2000开始研究,但是到2003年才出版文章,所以我们出版蛮快的,这也是价值的一部分。这就是之间的差别,比如我现在看一本书,他是2004年的调查,非常好,但是2010年才出版,那么我们说中间有没有发生事情?我们是新闻的,也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所以我们怎么写文章的?那个时候,我看看,你看过我们的clippings嘛?
但我们就是继续用劳达一的方式,他剪的那些文章,然后贴在一张纸上,这些资料多得很,然后现在好像电脑化了,这个是我们在社文中心做的,很多很多。
那你要写文章,你要怎么做?先选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大概是重要的,比如教育改革,好了,你去看看教育类的档案,这么多的文章,你要看这些文章,然后再写出分析来。所以,作这个clipping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些资料当中有一些非常宝贵,很有价值,但是因为数量太多太多。比如说,人民日报是我们以前都要看纸本,后来就是上网,还有不少消息都可以透过网络取得,所以,这个clippings没有这么大的帮助,没有像以前的价值这么大。不过,很明显的就是以前没有那么多clippigns,比如有一个法国人,研究哲学的,他到我们那边去,那我们说好吧你要什么,他当时就跟我们要有关人口的clipping,在那个时候这是很有价值的。可能在台湾,还有,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把报纸电脑化,没有太多网络资料。
其实,如果clippings如果准备的好,可以看的快。像我可能慢了一些,那现在我用网络找资料,我发现我有很多,比如,我们说统计,那以前统计学可能一年出一本书或什么,现在变成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都有报告,这就不一样了。可是,至少,我说到1995年左右,肯定还有它的价值。那最后CNA的价值,我去大陆工作离开了以后,可能他们有一些不一样,不过这是南耀宁可以跟你解释的,他做了很多。这些改变,不一定是我特别喜欢,但是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可能那个时候他们用人民日报,用的比较多,因为南神父每天都很仔细得看,这个人民日报。但是否,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这个人民日报我在台湾我没看,而是看地方报纸。也就是南神父专门看人民日报之类的大报纸,而我看地方性的报纸。可是,对我来讲,地方报纸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方面是有他的价值。
那谁看呢?读者是谁呢?有的时候,有人因为他们去大陆经商什么的,或是他们在那边有亲戚啊,他们说“喔,我了解我知道”。这些人可能有一大家族的
人在陕西,知道亲人之间谁谁谁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说“你了解没错,但并不一定能有足够的观察和洞悉。”不过另外一方面,的确是,如果有人去某一个农村,是一个小城市,他有直接的了解一些很重要的发展、情况。他光是看报纸,要注意,还是有一些实际情况的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去大陆看看。基本上不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现象出现,但是还是可以多了解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一点点困难,不过这个困难,现在还是有。我在大陆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面,那现在我去旅行,去农村或是一些小城市,跟当地的人来往,那有些不同的看法,一些新的,不是新的了解,不过,注意新的现象,比如刚刚说的家庭啊等等。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CNA有什么价值,新闻的这个价值是很重要的。可是所谓的新闻,并不是记者撰写的角度、方法,而是“他们说什么话”,这个是CNA
的价值所在。第二,另外一方面是,继续引起别人的注意,中国各地的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等等,避免太快的说法,“你说的对,但是…”或是“如果你说
的对,那你给我一些根据”。这个是很多人,比较难接受的,“喔,这个我知道”,可是你知道某一个地方的,但不代表这是中国整体的、普遍的现象。我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是否,很多人接受,我刚说的这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个时候觉得很重要,避免片面式的说法,或是没有根据的言论。
刘家正来之前,我们的确都是外国人作。所以可能,有一些中国人说“我知道中国,这是我们的国家”,没错,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所以现在没有这个问
题。这个大概都是80年代的。80年代有不少人台湾人到大陆、香港去,所以大概他们都知道这个价值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这样的分析,可能有帮助。所以CNA有一点在学术和新闻中间,近似于一种报告,不是太学术,也不是太秘密的消息,诸如“我认识某个人,他跟我说什么什么”,那刚好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态度。那另外一个价值是对我本人的,我学了很多。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继续看中国政府上面有谁,谁当什么部长啊等等的,我没有,但是这几年我看报纸都可以很快进入状况,帮助很大。
问:后来神父当社文中心主任,那时候接任主任有没有对中心有什么想法?
答:那个时侯已经停刊了,所以CNA已经结束了。我们那个时候就停止订报纸啊 什么的,改做clippings,不过,我的想法是我们要继续跟大陆交流,所以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是跟社会工作系合作并密切联系。那说实话,那时候社文中 心的方向,不是那么清楚,而且我做了三年主任。那为什么我做那个主任,没有 别人嘛,很简单。所以,我们是跟林桂碧一起合作的,还有辅大社会系的范丽珠 老师,那她有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我们主任关秉寅,我们参与一个好像是西药 公司要我们做的一个研究,关于台湾宗教方面的问题,就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我那个时候作的部份,我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看在台湾的中学教科书的分析, 也就是台湾怎么介绍西方文化,就做这个比较文化。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宗教方面,这个不是我做的,这是关秉寅作的,他 做一个问卷。那时候就请韩丽珠老师帮忙,我们请她大概是一个月,忘记是哪一 年,她看我们作的研究,她问这个问卷可不可以在上海作,于是我们也去过上海, 访谈一些学生,就这样完成那位学生的硕士论文。因为当时比较敏感,所以他不 敢说和我们一起合作,就是这个关系。这个也蛮好的,年轻人就喜欢。 我们那个时候,去上海几天,去帮忙看看他的情况。那关系怎么样呢?不是 那么顺利,老实说,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有另外一次,我们请大陆的大学社工系 系主任到台湾来待个几天。每一次我们要他们给我们做一些演讲,他们都婉拒了。 因为我们预算有限,所以不能开销太大。我们辅仁大学是不错的,但是不是最出 名的一个大学,所以大陆大学也是看看。我记得,在社会工作方面,在中国大陆, 有些人是有点怀疑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有最近的推动,不过有一个老师, 我们去访问他。所以那时主要的事情是推动这些交流,做得多少,不知道。不过 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想了,是不是社文中心,还要继续下去等等。
我离开之后是雷敦龢,他做的怎么样是另外一个方向,他做的是跟学生进行 一些互动,研讨会。不过,和大陆是不是有关,我想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往这 个方向作。 14 我们有一点事情是,就是一学期两三次,有一个小座谈会,关秉寅在这方面 谁都认识,我们请一个人给我们对谈,是不是和大陆有关?往往是有。比如我记 得我们有一次请那个,台大某一系的一个老师,他给我们介绍一个问题,然后我 们再提出疑问。这是学术性,但是我们也不是很隆重,你来我们很高兴,可是我 们都是平等的,这个机会蛮好的,真的是所谓的学者,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没有 录音,也没有什么记录的,所以非常自由,你可以自由发挥,以任何方式。所以 这个是还蛮有趣的。那时候我当主任时候,比较有困难的是,我不认识这么多在 台湾的学者,不过我们做的一两次还可以。不过那个方向,相当的模糊,而且那 个辅仁大学说,学校太多研究中心,那个时候就是管理学院已经独立了,那法学 院要和社会科学院分开的,那你说我们属于谁?当时有一些预算方面的问题,以 后就容易有困难。
另外一方面,我在那边已经十年了,我说,可能需要另外一位人,有新的想 法,有新的活动啊。如果我当初继续下去的话,我不会走这个方向,我会继续和 大陆保持一些研究、学术关系,不一定我那个时候一定接触一些基金会也是有可 能的,最后,我就换工作了。可以这样说的,我那个时候说,我们的中心就要跟 大陆保持一定的关系,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够帮助大学各个部门的在一起,或许可 以一起推动一些计画。可是你知道在大学里面,我不是说什么不过大学里面大概 每一个系,大家都是小小的,不太关心其他领域的人在作什么的。所以,本来一 个方向,就是我们是综合的推动、帮助,有这个有那个(单位),我们就是和社 工系,在一起合作。所以我们中心,有的资源,不管是我们有的还是你们的,无 所谓,反正可以一起用,一起合作。那其他系里面,我不认识。没关系,大学就 是这个样子。包括大家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关闭中心)。我们贵是贵,可是没 有那么贵!特别是没有刊物以后。还有可能,那时候就是绿党,比较敏感,所以 和大陆的那个也不是那么那么有兴趣。可能我讲得有点过分,不敢说的。如果我 们是在香港,或是换到这来,那方向会完全不同。那为什么长上决定要到台湾去, 不知道。
问:如果CNA当初,搬到台湾,可是不是搬到辅大,可能是台大,那可能就可以 解决研究人员的问题?
答:会,不过台大大概不会感兴趣,那个时候是耶稣会的决定,不是CNA的决定。 因为本来,啊对我忘了一个事情,我们的CNA,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我 们的自我,我们说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大学,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公司或是基金会 什么的,完全没有。所以这个没有广告,完全没有。那我们去台湾辅大,因为那 个时候辅大行政方面还没有合一,所以耶稣会可以决定这个。所以,虽然是学校 给我们预算、钱、支持,可是这个是耶稣会的决定,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自我。可 是这个事情越来越难。 因为我们当初没想到,我们可以搬到Macau来,相当程度可能的。但是会不 会受欢迎,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好像没有考虑过Macau,我现在想起来,咦 15 为什么我们没有搬到这边。好,来台湾,至少有人说,我们有一个学术环境。只 是我们发现,除了关秉寅之外,林桂碧啊,没有受到多少人特别关心。可能是我 们做的不够。可是另外一方面,台湾跟大陆越来越远,所以大环境上发展也不容 易。最后决定关闭中心的决定,我也没实际参与,因为当时我已经不在台湾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和中心有联络,应该是在结束前夕,跟雷敦龢联络,他说他还有 一年的时间。
问:请问神父,当时为了维持CNA的独立,那么资金来源主要是耶稣会嘛?
答:对。喔不过,我们写什么东西,耶稣会就不管的。因为他们的立场很清楚, CNA这个是学术性的。那这个经济方面的讨论,当然不会有困难,那政治方面可 能就没这么明显了。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歪了,或是不赞成我们的 说法的话,可是我们会自问,那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要求他们每一次每 一期都先看过、审稿。劳达一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这个样子。耶稣会这方面 很开放的。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满意,长上不满意,或许可以换人经营, 或是说对不起关门。那就完了,那我们没话讲了。可是,如果等于说,他要我们 继续做的,我们就做。至少,我在参与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干涉我们写 的东西,没有,没有。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别人作的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避免宗教方面的问 题,特别是天主教内部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碰。所以可以发现这些问题是没 有的。偶然会有宗教组织一些政策的讨论,可是宗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尽量 避免。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的方向,因为这一方面,教会有足够的人来研究。就 是在香港有一个“圣神研究中心”,他们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就说“你做吧”。
- 访谈时间:2010年8月16日,10:00-12:30
- 访谈地点:澳门岗顶前地,利氏学社会客室
- 访谈者:林凯蒂
- 受访者简介:狄明德,法籍耶稣会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社会学博士,曾任辅大法文系、翻译所长,中国社会文化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以下简称CNA)主编之一,2003年迄今转任澳门利氏学社研究员、秘书长。
本文摘录自台大政治学系网站
※版权均为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来信吿知,我们会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