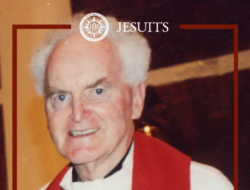文/李天綱
雷煥章(Jean Almire Robert Lefeuvre,1922-2010)神父是法國人,出生在西南城市勒芒(LeMans)附近的小城高定(Chemire le Gaodin),父親還是當地的市長。在勒芒,雷煥章上了耶穌會的中學,畢業以後就加入了耶穌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軍作戰,被俘後關進德軍的集中營,九死一生。1946年,在蒙彼利埃大學哲學系畢業後,立志來中國。後來,他經常說:”前往中國並非為著傳教,因為牧靈工作我留在法國便有得做。我去中國,是因為我要學習中國人看待人生、世界的眼光……。”雷神父久住中國,稍稍及老,人稱”雷公”,他就扮個臉,笑笑。
不傳教的法國神父,熱衷中國文化,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即使到”二戰”以後的新時代,哪怕是有著利瑪竇寬容傳統的耶穌會,對於如此”跨文化”而來的”學問僧”,大約也是”蠻吃酸”的,難以招架。1947年10月,雷煥章到了上海。在徐家匯修院,他們幾個”新潮”年輕人被法籍老神父視為另類,受到了冷遇。此後,他們去了北平修院。在那裏,設法進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插班念三年級。同班聽課的有王太慶(研究柏拉圖)、陳修齋(研究萊布尼茲)。還有一位鐵杆哥們,鎮江人謝邦定,中共地下黨員,任第一屆全國學聯主席。他們的老師,則是著名的康得哲學專家,後來當過北大哲學系主任的鄭昕教授。在北大,終於”與年紀相仿之中國人為友”,看雷煥章多麼渴望進入中國的學術界。
倘若歷史並不中斷,雷煥章會和北大哲學系1950屆的同學一起畢業。北大多才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希望成為新一代的哲學家。中國文化在百年激蕩中更新,思想激進而混亂,宏闊而貧乏,急需一大批哲學家厘定乾坤。按雷煥章的回憶,他們班上一共30個同學,除了五六個跟國民黨之外,其他要麼是中共,要麼是親共。”原因無他,只因他們深感高官腐敗,國家紊亂,殷盼新政府出現。”正是在這種氛圍之下,大部分同學畢業後都”參加革命”,像謝邦定那樣。像王太慶、陳修齋等留在學術界,支撐北大、武大哲學系的,只寥寥幾個。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段德智教授,曾經親口告知,說陳修齋先生在北大和歐洲人切磋萊布尼茲。”歐洲人”,當即雷煥章等人。
1949年到1952年,雷煥章離開北京,在上海的徐家匯耶穌會總部又住了三年。在上海,他換了一種方式親近中國文化–和本地年輕修士交朋友。上世紀40年代,上海天主教會培養出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張伯達、朱洪聲、朱樹德、金魯賢,他們家境富裕,眼界寬闊,學術素養好,且志向遠大。徐家匯的語言,除了法語,就是上海話。雷煥章剛剛在北大學了普通話,又努力練習上海話,他說:”上海籍中國修士對我極好,然跟他們相處,可得講上海話,普通話是行不通的。我上海話一旦說到了辭窮處,便趕緊以法文接濟救急。”世界上大約只有利瑪竇這一派的傳教士,才真正懂得方言的厲害。這一派人主張:若要瞭解對方的文化,先要學習對方的語言和文字,就如同進入一主權國,先要取得護照和簽證那樣。雷煥章先學普通話,後學上海話,再到臺灣學習閩南話,研究甲骨文,都是循著這條”方言”路徑,進入了豐富多樣的中華文化。
雷煥章的上海話之道地,臺北有名。2002年夏天,在臺灣大學開會,古偉瀛教授領著去看雷煥章,說是要讓神父有個溫習上海話的機會。雷公對上海很懷念,晚年動情地說:”在上海的那段日子,中國神父助我明白了中國人許多根深蒂固的觀念。認識這批年輕的中國神父,對我影響極巨。相較之下,滬地那批法籍高齡神父對我反倒顯得可有可無。我與年輕的中國神父同窗剪燭,凡計三年,誠為三生有幸。”不久,形勢變幻,雷煥章依依不捨地離開上海。在菲律賓流落數年後,於1955年到臺灣,在台中編輯《利氏漢法大字典》,又一次浸淫在中國文化的體膚之內。
難以置信的是,雷煥章在42歲的時候,方才發願學習甲骨文。1964年,為了編輯《利氏漢法大字典》,雷神父聽從老朋友顧從義(Claude Larre,1919-2001)的意見,承擔漢語古文字的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學習甲骨金文很少半路出家的,收集、謄錄、釋讀、記憶,會耗費大量時間,非年輕從事,難以建功。復旦歷史系有胡厚宣先生留下的甲骨學,我們一群人也曾跟著吳浩坤老師擺弄過一陣子,剛剛知道這門學問的艱深,便知趣地逃走了。沒有”童子功”,雷煥章也弄甲骨文,但他居然能弄得像模像樣。自1971年起,雷公全身心投入了古文字學。他住在臺北市杭州南路”震旦中心”,杜門謝客,寒窗苦讀,潛心研究。雷煥章的路徑,主要是摸索甲骨文、金文在商、西周、東周時期的不同用法,”力辨各代間之異同,務求收攝提綱挈領之功。”雷神父的甲骨學,學不在功力之積累,而在方法之正確。他說:”我個人以為,真欲研究甲骨文,憑藉記憶固然重要,研究之方法論更是不可或缺。”摸准了方法,不妨八十學吹打。雷神父把”方法論”引入甲骨學,他的治學經驗,對”中年變法”的學者,是個鼓舞。
雷煥章另闢蹊徑,發揮所長,編輯了《法國所藏甲骨錄》《德、瑞、荷、比所藏的一些甲骨錄》和《甲骨文集書林》,對甲骨學確有獨到之貢獻。三書所收的甲骨,雖不如大陸各處所藏總集那麼浩繁,但拾遺補缺,頗有可觀。憑藉這些成果,”文革”過後,雷煥章和北京、上海的甲骨金文學者,如夏鼐、胡厚宣、馬承源、李學勤、裘錫圭等教授都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研究中國古文字的學者,老外並不多,雷公一副外洋人樣子,經常出現在祖國大陸和台、港,以及美歐諸國,讓這門學問看起來中外熙洽,興味盎然。
不懂甲骨學,無法對雷煥章的古文字學做一個行內的評價。不過,讀到雷公對於幾個重要甲骨文字的解釋,倒是也有啟發。比如,對”帝”字字形的分析,雷公不同意郭沫若的說法。郭說”帝”是一朵鮮花,象徵生命的來源。他則認為:”‘帝’字極可能象徵著龍頭,因字頂端‘▽’部分,正代表著宏偉事物之首。””帝”字的原型,含義近”龍”,和”鳳”相對。甲骨文”鳳”字的頂端,也有一個”▽”作冠首。雷公認為:”帝”字的用法,後來有了改變,他同意裘錫圭教授的觀點,”帝”與”父”通。在商朝人的祭祀中,”‘帝’的概念已極為清楚,亦即它是天上的父,是萬有生命之源,且是整個宇宙之主”。這個說法,雖然帶有耶穌會利瑪竇”上帝論”的痕跡,但實在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後半生研究漢文字,對於”中文的未來”自然很是關切。中文之美,如同法文之美,千萬不能湮沒,這是雷公晚年的內心牽掛。他說:”中國人自應保存自身文化特色……我個人則希望不要去除漢字,最好對其加以妥善保存,因中國文化早已同漢字難分難舍。為了整個中國文化之長存不輟,漢字自應保存。”求”進步”,謀”發展”的中國人,曾經拿自己的文字來開刀,把各處的方言作犧牲,這樣的歷史,實在是個教訓。雷煥章的忠告,我們應該聽一聽。
前幾次我到臺北,路過敦化南路一段的”利氏學社”,都會去雷公的辦公室張望一下,和他這位”老上海”隨便說上幾句上海話。這一次來臺北,雷公參與創辦的臺北利氏學社遷到了辛亥路一段的耕莘文教院大樓,他自己卻在2010年9月去世了。在上海,收到過雷公去世的E-Mail訃告,心裏存念,要祭奠一下。這次在利氏學社裏,看到的只是雷公留下的藏書,還有大功告成的《利氏漢法大字典》,面對遺物,惟有默禱。88歲的”米壽”之年,逝在臺北,葬在彰化靜山墓園,魂屬中華。邊上人說,雷神父生前做夢,說的是中文。在天堂裏,應該也是和他的中國朋友們一起,說著中文–上海話、普通話、閩南話,或許還比劃著那一方方–甲骨文吧?